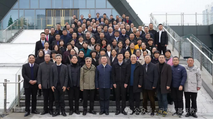梅贻琦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于赴美留学期间,受洗成为基督徒。归国后出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后又在清华大学长期担任校长。不论是教育理念、行事作风,还是道德品格、人生旨趣,他都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实际上,梅贻琦多年执掌清华大学成绩斐然、深得人心,与其基督徒身份和卓尔不群的教育思想有一定的关联。
“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十五岁进入天津南开中学,1908年成为该校首批毕业生,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被保送至保定直隶高等学堂就读。翌年,又考取清政府游美学务处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居于清华校史上“史前生”或“直接留美生”之列。
1909年11月,梅贻琦抵达美国,并于次年进入马萨诸塞州吴斯特工业学院(WorcestorPolytechnicInstitute)电机系学习,求学期间皈依基督教,成为基督徒。曾经与梅贻琦在吴斯特工业学院同住一室多年的同学杨锡仁回忆,梅贻琦学习成绩优良,性极温良,并且笃信基督教。他说:“梅很少错过周日的礼拜。有时,我们同马歇尔一家去协会的教堂;有时,我会在星期日和周去邻近的波士顿参加1910级同学会,他则和张彭春一起去南吴斯特作礼拜。1913年春天,梅、张和我加入了马萨诸塞州的基督教青年会北美联合会组织。”可见,梅贻琦经常参加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活动。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相当社会化的组织,其立会宗旨“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一语,乃取自《圣经》马太福音二十章28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简而言之,就是强调为社会、人群服务。
1914年,梅贻琦获工学士学位。因家庭经济困难,他不得不放弃攻读研究生的机会,回到中国。是年10月,梅贻琦被聘为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直到1915年9月回清华任教。
这一时期的清华有着颇为浓厚的基督教色彩。美籍教师自不待言,中国教师也多为基督徒,学生中虔诚信仰者亦不乏人。清华的校长、教务长,要能在清华待得长久,除了留美的条件(后期又加上是否为清华毕业的条件)之外,是否为基督徒也很重要。清华校内的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2年,当时会员约占全校学生的半数,归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直接领导。为了宣扬基督教教义和帮助学生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基督教青年会组织了许多课外查经班,每班不超过十人,每周一两次,读英文版《圣经》,学生都是自愿参加,由中外教师担任指导。梅贻琦曾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干事,因此也应邀指导一班。社会学家吴泽霖教授和潘光旦教授回忆说,他们都曾参加过梅贻琦所指导的查经班。
1921年,梅贻琦再度赴美进修,入芝加哥大学研习物理,获硕士学位。在遍游欧洲大陆后,于次年秋回到清华。梅贻琦与刘湛思、沈隽淇、朱斌、林武煌、胡贻谷六人游历欧洲之后,写下了《欧游经验谈》一书。梅贻琦等人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之托,考察欧洲的中国青年留学生学习和生活状况,并且极为关注欧洲各地基督教青年会的运作:“不但欧洲各国的政治、民情,就是在欧洲留学的数千中国青年处境怎样,我们也觉得极其模糊,无从做有效而互相提携的工夫。”
在这本游记中,梅贻琦等人介绍了五个基督教青年会,即伦敦青年会所、全英青年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设于巴黎的留法学生青年会、世界青年会事务所、和美国青年会事务所。在介绍全英基督教青年会时,他们着重评价基督教青年会的创始人卫良佐治(GeorgeWilliams)以及时任全英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耶波氏(SirArthurYapp),指出“他是一位勋爵,为人精明强干,但很和气知礼。学生运动总事务所是在一处很清静的地方,……办事人的精神都很好。”这几处笔墨颇值得玩味,作者不是随意介绍人物,而是着意表达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的“气质”和“精神”。这无疑是在阐明基督教青年会健康、向上和服务于人的内在追求。
从游记中还可以了解到,梅贻琦等人考察各国基督教青年会的情况时颇为细心:“(全英青年会)最近在市外工厂繁荣之区普兰斯笃开办的红三角俱乐部,倒是青年会的一种破天荒事业。他所注意提倡的各种事工,莫不以迎合人生繁殊的需要为唯一目的,它的会员是不分男女一例看待,会所内举行的运动、演讲、影戏、跳舞、音乐等都是活泼而有深意,能使庄重有礼贯彻于浓厚的兴味之中,所以我们参看了以后,得了良好的印象,以为他的计划和程序是健全无害的。至于他为会员筹划讨论的问题,如工业问题、社会主义、美术问题,……不是对人生的需求便是专学学理的研究。……在试办之中颇得一般的重视和赞许,预料他必能日益发达呢。”
在这番记述中,梅贻琦等人对基督教青年会的羡慕和赞许之情溢于言表。作为一位深受基督教青年会影响的近代教育家,“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精神贯穿于梅贻琦一生服务清华的努力之中。而这样的努力和奋斗,恰恰较集中地体现在“中西合璧”四个字上。
中西合璧的真君子
曾掌管清华体育部的马约翰教授在祝贺梅贻琦任教清华学校二十五周年的贺词中称道:“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具备了中西人的优美部分。”正如他的逝世祭文中所写:“先生之行谊,本乎中国文化之渊源,而学术则造乎西洋文化之峰颠。观乎先生之仪型多士,我先民中体西用之理想在焉。”这种由“中国文化之渊源”而至“西洋文化之峰颠”的“中西合璧”,在梅贻琦一生最大的“杰作”——清华大学,得到了最为明确的体现。
梅贻琦见证了清华从一个单纯的留美预备学校,发展成中国顶尖的大学之全部过程。期间,既经历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黄金时期”,群贤毕集,冠盖满清华,又有抗战八年时期烽火连天仍弦歌不辍的西南联大时代,艰苦卓越,灯火传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清华校长”是梅贻琦一生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身份。以至于他后来谈及此事时,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琦自1909年,应母校第一次留美考试,被派赴美,自此,即与清华发生关系,受清华多方培植。三十二年来,从未间断。以为‘生斯长斯,吾爱吾庐'之喻,琦于清华,正复如此。”
文章〈大学一解〉与“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出自梅贻琦就职演说的名言,最能集中体现他的教育思想了。在〈大学一解〉开章中,梅贻琦采取中西比较的方式,论述大学产生的世界性意义:“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而对大学的历史源流,梅贻琦则清醒地认识到:“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th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
可见,梅贻琦认为中西大学的本质、目的都在于“一己之修明”。而“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实际上也是根据孟子所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变化而来。综而言之,梅贻琦的教育思想与对儒家以及西方的文化经典汲取是分不开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常常自称“吾从众”。他在治理清华学校时,采取的正是“吾从众”的治校方针。“月涵先生的民主作风也是值得我们钦佩的。他主持清华校政时,始终保持教授治校的原则,遇事公开讨论,集思广益,择善而从,决不坚持己见,独断专行。”
而这种教育管理思想也“不是凭空产生,亦非是在清华作教授时产生的,而是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一思想得益于他早年留学美国”。他的“吾从众”真正本质是追求西方式的民主和法治,深受清华师生的赞誉。无怪乎朱自清曾言:“清华的民主制度,可以说诞生于(民国)十八年。……梅月涵先生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他使清华在这七八年里发展成为一个比较健全的民主组织。”
梅贻琦自执掌清华之始,就以“吾爱吾庐”的态度爱护学校。在清华每一笔物资的使用上,梅贻琦几乎达到“严苛”的程度,决不随便乱耗费一分钱,决不为己谋一丝私利。任清华留美监督期间,梅贻琦尽可能为清华节省每一分钱,简化监督处的办事机构,不仅辞去司机,自己学开车,而且还让夫人韩咏华兼作厨师,不再另付报酬。1931年梅贻琦出任校长,按规定住进了清华园里条件最好的甲所住宅。可是,他放弃校长的特权,家里工人的工资由自己付,电话费亦自己来付,甚至连学校供应的两吨煤也不要。可遇有他认为应当为清华学校花钱的地方,梅贻琦往往又异常“奢侈”。他曾说:“清华有点儿钱,要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
一语九鼎的“寡言君子”
梅贻琦有一个显著而广为人知的特点:沉默寡言。他工作中话少,与朋友相处话少,即使对家人、子女同样也是话很少。他在任何公众场合都是听得多说得少,就是在不得不发言时,也是把话说得很慢,但逻辑非常清晰,也很少有断然的结论,但他往往在关键的时刻能够一语九鼎,做出断然的决定。清华人评价“他开会很少说话,但报告或讨论,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争辩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又说他“平时不苟言笑,却极富幽默感和人情味,有时偶发一语,隽永耐人回味。”国学大师陈寅恪则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贻琦慎于发言,遇到问题时,也总是先征求对方意见“你看怎么样?”当得到同意的回答,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语气和缓地说,我看还是怎样怎样办得好,或者说,我看我们再考虑考虑。他谦虚平和的待人态度,即使有不同意见者,内心也会有受到尊重的满足,不会产生怨懑。有学者认为,西南联大三校在抗战时期纷繁复杂、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能够求同存异、同舟相济,共创教育史上的辉煌,应该说与梅贻琦的领导风格和个人修养是不无关系的。
梅贻琦说话少而严谨,写东西同样言简意赅,提纲挈领。他批示的许多报告就是两字“照办”。据他的夫人韩咏华回忆,当年梅贻琦求婚的“情书”也是特别简单,切中主题。梅贻琦回国到清华任教后,提亲的人就络绎不绝,因要赡养父母,供给弟妹们求学的费用,他全部回绝。直到近三十岁,才经严修从中介绍,与在南开幼儿园任教师的韩咏华见面。当时,由韩咏华的表哥出面请男女双方吃了顿饭,算正式认识。隔日,梅贻琦写信给韩咏华,以示求婚。韩咏华将信拿给她的父亲看,韩父看到措辞平淡,寥寥数语的“情书”,便说“不理他”。韩咏华遵父命没有写回信。梅贻琦等不到回信,又写信,责怪道:“写了信没有回音,不知是不愿意,不可能,还是不屑于……”,韩咏华接到信后又拿去给父亲看,没料想,韩咏华的父亲读过信后接连说道:“好!好!文章写得不错。”同意了女儿与梅贻琦的交往。数月后,两人订婚。韩咏华的一位同学听到消息后,急忙跑来韩家告诫韩咏华说:“告诉你,梅贻琦可是不爱说话的呀。”韩咏华以一种凛然赴难的语气说:“豁出去了,他说多少算多少吧!”
廉洁俭朴的一校之长
“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用这八个字概括了他对清华的深厚情感。他长清华,爱清华,就要使清华在“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各事更应力求节省,期以最廉之代价,求得最高之效率。”梅贻琦言行一致,上任之后,住进清华园甲所(法定校长住宅),按惯例许多生活开销由学校供给,他主动放弃特权,家里佣工的薪水、电话费以及学校每月免费供应的两吨煤全部自付。
他不允许家里任何人乘他的汽车办私事,夫人要坐只能顺路搭便车。他写报告,公函的草稿纸都是用废纸的反面。他说:“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1938年到西南联大后,梅贻琦与普通教授一样租平房,住所窄小简陋,并将校长专用车交给学校共用,外出办事,路近则安步当车,路远则搭便车,或坐人力车载一段路。
1940年以后,滇川各省物价飞涨,教师们的薪水不能按时发放。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常有发生,梅家生活也十分清苦,经常吃的是白饭拌辣椒,连青菜都买不起。梅夫人做松糕到冠生园寄售,摆地摊出售儿女们小时候穿过的衣裤以贴补家用。有一次,儿子梅祖彦的近视眼镜镜片摔碎了,影响听课记笔记,好久无钱重配。小叔叔梅贻宝(燕京大学校长)赴美前到昆明探望哥哥,看到侄子闷闷不乐,一问才知原因,就出钱为侄儿配了一付。
联大给教师谋福利,梅贻琦主持制定校规规定:学校3个常委都不能享受(另两个人有兼职收入)。教育部曾发给联大一笔学生补助金,梅家有4个孩子在联大读书,按规定有资格领到补助金,梅贻琦不允许自家孩子去领,而把补助金让给更困难的学生。
梅贻琦所行之事处处为学校打算,俭朴作风给同行留下深刻印象。1941年7月,梅贻琦与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等在成都办完事后,准备转重庆回校,梅贻琦联系买好飞机票后,又得到可以搭乘邮政汽车回昆明的机会。邮车不仅比飞机晚到一天,一路上还要遭受日机空袭之危险、山路颠簸之苦,但可以为学校节约两百多元钱,梅贻琦毅然退了飞机票,一行3人乘邮车回到了昆明。
梅贻琦晚年病痛卧床,面对死亡时,曾说:“耶稣爱我,耶稣关切我,耶稣保佑我,所以耶稣救我。”又说:“神什么事都知道。”除了虔诚信仰之外,梅贻琦更用一生的行止实践基督徒的精神。他的寡言慎行、自律甚严、忍耐宽容以及诚实的品格,其实也正是一个基督徒的品格。
从梅贻琦身上不难看出,基督徒与儒者双重文化身份,最终在个人道德和修养层面获得了会通和结合。他很自然地接受了二者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规范以及行为处世的要求,所谓“中西合璧的真君子”,即是最好的说明,而梅贻琦的清华校长形象,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儒者和基督徒相融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