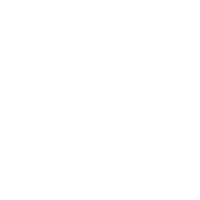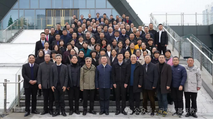今年是孙中山先生150周年诞辰,在这纪念的时刻,重提基督教与孙中山及中国革命的关系,是对历史与孙中山先生的尊重。尽管不能过分夸大基督教在孙中山思想形成与辛亥革命中扮演的角色,但基督教在其一生中留下了厚重的痕迹,在其思想光谱中可见基督教参与的影子。同时,基督教会在中国早期革命中的参与也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许多基督徒成为了革命力量。这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遗产。
孙中山先生真正触摸西方社会的起点,是1879年赴檀香山,在兄长孙眉的资助下,开始接受西方近代教育。而其入读的第一所学校,就是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所办的意奥兰尼学校。该校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每天的早晚经课,孙中山在这种规律性宗教生活的潜移默化中度过了三年学习时光,并开始表示出对基督教的好感。1883年,孙中山进入瓦湖书院预备学校学习,宗教教育是该校课程的重要内容。孙中山延续了他对基督教的兴趣,积极参与该校美国纲纪慎海外传道会夏威夷分会传教士芙兰·谛文主持的主日学和基督教青年会。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经历,以及接触到的西学和基督教,作为一笔财富被带回了中国。回国后,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对比催生了其对祖国命运的忧虑。1883年冬,孙中山进入香港英国圣公会办的拔萃书室读书,其间结识了美国纲纪慎会传教士喜嘉理。喜嘉理为孙中山的宗教热诚所打动,最终在1884年5月4日为其施洗,取名“日新”。孙中山受洗入教后,还积极鼓励并介绍好友陆皓东及唐雄入教。
1884年中法战争的爆发,开启了孙中山先生救国的旅程。他认为,医学救国是一个适当的选择。1886年,孙中山求助喜嘉理牧师,将其介绍给广州博济医院院长、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嘉约翰,后顺利进入该院、开始学医生涯。在此学习一年后,1887年10月,又转入伦敦布道会协助下创办的香港西医学院。
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失败后,开始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早期在其身边集聚的很大一部分革命同志都是基督徒,包括陈少白、郑士良、谢缵泰、左斗山、王质甫、陆皓东、区凤墀等。他们作为晚清革命的领导者与参与者,成为中国革命的先驱。与此同时,许多基督徒尽管未参与革命斗争,但成为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在财力和组织等方面为革命提供帮助;许多教堂和教会设施也成为革命党的掩护机关,为革命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这些成为当时中国革命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在辛亥鼎革之际,基督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武昌,黄吉亭、胡兰亭等在圣公会内部组织“日知会”,一部分具有基督徒和革命党双重身份的同志相聚其中,成为革命的宣传和实践机关。刘静庵、曹亚伯、张纯一、殷子衡等基督徒是中坚力量。同情中国革命的传教士也对革命者伸出了援助之手,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主教吴德施给他们的活动予以了积极支持,鼓励他们进行爱国运动。
当时有评论说,“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教会的影响;教会, 通过 过去和现在的影响,成为了主要的革命因素之一。”“新共和国建立者的目的在许多方面不仅与基督教的理想一致,而且公开认为得力于基督教”。
革命成功后,在面向教会的演讲中,孙中山也多次表扬基督教的贡献。1912年9月的一次演讲中,孙中山说,“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力,乃教会之功。”后来他又指出:“吾人排万难冒万死而行革命,今日幸得光复祖国。推其远因,皆由有外国之观感,渐染欧美文明,输入世界新理,以至风气日开,民智日辟,遂以推倒恶劣异族之政府,盖无不由此观感而来也。而此观感得力于教会及西教士传教者多。”
直到晚年,孙中山仍然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徒者实多。”但作为同道,民国政要徐谦曾询问他作为基督徒为何不上教堂作礼拜,他回答,“我是革命党,只心中崇拜”。他担心革命倘若贴上基督教的标签,会影响到革命的号召力。
孙中山临终前,在病榻上仍坚称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其去世后,1925年3月19日,在北京协和医院礼拜堂举行了盛大的追思仪式,燕京大学教授刘廷芳牧师主礼,并奏圣歌,国民党内基督徒徐谦也发表宗教性悼词,将其生平和志业与基督教联系起来。不过事后,有党内要员强调,不能让基督徒特别是传教士将追思礼拜用作宗教传播的凭藉,而应视为一个基督徒生命中的例行事务。
虽然基督徒身份不可能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和基督教的事业联系起来,但是,基督教确实在当时中国革命过程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这说明,中国基督徒并未因为信仰“洋教”而疏离爱国主义,在近代内忧外患的处境下,他们同样关心祖国的命运。辛亥革命中的中国基督徒,他们是爱国者,是“爱国爱教”的典范。
原文: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基督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