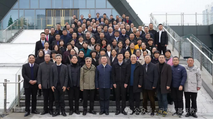在保山福音自愿戒毒中心成立十周年暨新址搬迁典礼上,同工任一超介绍了福音戒毒工作的三点意义,即:福音戒毒既是一种外来传承,又是一种自主创新;福音戒毒既是一项基督教实践,又是一项社会公共事务;福音戒毒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反科学。
首先,任同工认为,福音戒毒本质上是一项以戒毒为现实目标的基督教实践,既是一种外来传承,又是一种自主创新。他介绍,该实践最早源于19世纪西方传教士兴起的针对中国人鸦片瘾症的救治。当时外国差会普遍采用西医传教的策略,但唯独在鸦片瘾症的治愈当面,西医始终不怎么见效。因此,传教士们不得不以一种纯粹的基督教信仰方式来看待并尝试对鸦片瘾症进行救治,这基本上可以算是基督教戒毒实践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探索和尝试。随后,西方传教士逐渐撤离中国,他们的基督教戒毒实践也随之在中国销声匿迹。
大约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现代中国吸毒问题的加剧,以及社会各界逐渐对戒毒困难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基督教也自发地开始根据自身的信仰视角和教会资源,在戒毒方面进行尝试和思考。尽管西方传教士早年在中国开展过戒毒实践,能够为现代中国教会提供参考和依据,但除了有一些史料类和传记类的零星记录之外,完整的内容和资料基本上已无从考擦。因此,任同工分享,中国基督教会能从那场传教士的戒毒实践中实际获得的,也只能是一种信仰精神的传承。
“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福音戒毒’基本上是由中国教会经过自身探索而创立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戒毒模式,国外虽然也有基于基督教信仰的戒毒疗法,但不像中国教会目前的情况有一种像‘福音戒毒’这样统一而通用的概念和模式,甚至在国外并没有‘福音戒毒’这种固定的概念名词。”任同工表示,“因此,‘福音戒毒’在严格意义上来说不仅不能算是西方基督教现成的舶来品,而且通过港台地区一些较早起步的‘福音戒毒’已经将分支机构开设到国外的过程,反倒使‘福音戒毒’的理念和模式影响到了国外。经过保山‘重生园’这十年来的工作,‘福音戒毒’如今在中国内地也逐渐达到了一种概念化和模式化的认知程度,这可以算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典型案例。”
其次,福音戒毒既是一项基督教实践,又是一项社会公共事务。任同工分享,宗教性的实践是指将信仰理念的内涵落实到信徒的生活环节,这原则上会与信徒在社会生活中的世俗性内容存在严格的区分。但事实上,如今的宗教实践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界限已经越来越难以划清。尤其在加尔文“天职观”的广泛影响下,基督新教应该是较早开始在世俗生活的领域对宗教实践进行思考和探索的。
“如果说早期传教士的戒毒实践还不能完全脱离西方传教的宗教性背景,那么今天中国教会开展的福音戒毒其实就已经属于地方社会实践的一部分了。”教会通过实践的层面与社会融为一体。对教会来说,戒毒目标既是宗教性的,同时也是世俗性的。”任同工说。
因为,戒毒工作原本只属于世俗事务,但在教会的参与下,它又同时具有了现实与超越的一种双重维度的意义。“随着福音戒毒继续的发展和深化,无疑将有助于在整个社会层面的意义上,为戒毒工作的探索和认识打开多重的维度,增强思考和创新的活力。在宗教实际与社会公共事务至今的协调与融合方面,戒毒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为二者实现了一次成功的结合。”
第三,福音戒毒既不是科学,也不是反科学。任同工分享,在今天这个时代,人们通常都会用科学来作为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可靠的标准。就戒毒工作而言,是否符合科学也是一种普遍的评价标准。但是,科学并不是我们实际生活的全部内容。拿西医和中医来说,它们各有一套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但是在我们的求医经历中,二者并不是互相对立的。
任同工因此认为,福音戒毒与中医的情形类似,它自身对成瘾和戒瘾有一套完整的认知理念这一点是与生物医学(西医)完全不同的。对于戒毒工作来说,并不是有特效药而不用,而事实上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种戒毒药物能够彻底治愈毒瘾。“福音戒毒从来不排斥生物医学的作用,但同时知道毒瘾的哪些方面是生物医学鞭长莫及的。福音戒毒充分地从基督教信仰中汲取了有效的资源,并提供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实践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福音戒毒并不是一种科学,但这种戒毒方式在提供自身独特的戒毒方案时,当然也需要包括科学在内的所有社会资源的配合与支持。在这个意义上,福音戒毒绝不是反科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