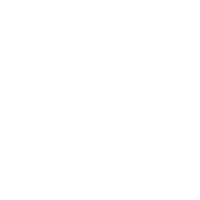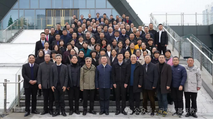在基督教古公教会的神学遗产中,迦太基的主教西普里安在捍卫救赎唯教会独揽的工作上贡献重大。他格外强调主教的重要性,正是因为主教乃使徒的接班人,所以主教们享有与基督赐给使徒们同等的权柄,当任何异端势力企图分裂教会或者教会内部的群体间发生冲突时,主教的重要性才会体现出来。[1] 但是,如果一位主教本身是异端,或者一位主教滥用职权,那么应该由谁来裁决本身具有裁决权的主教呢?西普里安虽然重视主教在教会中发挥的作用,也同时强调统一。当把统一与主教的作用联结在一起后,这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统一与主教联系在一起后,便产生了主教团。冈察雷斯说:“主教团只有一个,但他不是要全体主教服从于一个‘主教们的主教’那种性质的教阶组织,而是由于每一位主教体现出主教团的整体性”。[2] 也就是说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众主教之上的一个监督团体,而是主教与主教之间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互相制约的监督机制。[3] 正因为西普里安采取一种联邦式的主教制运作教会,以至于他不承认任何一位主教是所有主教的头。他曾反对罗马主教对其他教区的主教也拥有裁决权,尽管罗马教会及其主教在教会中享有某种优先权,但是罗马教会的优先权并不代表他可以拥有高于其他教会的权柄。所以当一位罗马主教试图将罗马的习俗强加给非洲时,西普里安反对道:
“我们中间无人可以将自己封为主教们的主教,我们也没有用专横的威胁逼迫同工必须服从自己;因为每一位主教在其自由和职权范围以内,都有自己正当的审判权利,他不能审判别的主教,别的主教也不能审判他”。[4]
可见,任何一位主教置身于主教团的统一性机制下,将不会存在一位主教以强权将其个人意志加诸在其他主教之上的可能。因为每当有一个意志企图影响集体意志或另一个个别意志时,主教团的功能便发挥作用,即以教会的统一性来施行审判,而不是由一位主教通过“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方式解决争端。教会的统一性时刻存在主教团里,主教团也时刻实践教会的统一性。正如冈察雷斯说:“统一性不是加在真理之上的事物,它只是基督教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离开了统一性就无所谓洗礼,圣餐和殉道,这种统一不是服从于一个主教们的主教,而是共同的信心、爱以及主教们之间的交流”。[5] 也就是说统一性不是异己和强权,而是对基督教真理的共同信仰和普遍顺从。它保证了任何分裂破坏它的一切企图都将在真理的标准以及所有主教因服从一个真理而凝聚成团的集体权威下化为泡影。倘若没有统一性作为主教团的根本保障,不仅主教与主教之间在管理上可能产生分歧,教会也因为主教之间的相互排斥而沦落为信仰混乱的小团体。在西普里安的著作《论教会合一》中,他非常强调教会应当时刻警醒,以防备仇敌的诡计。正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哪,我们不但必须防备公然明显的仇敌,而且必须防备施诡计行欺哄的仇敌”。[6] 而对抗这些明显的或狡猾的仇敌所依靠的有力武器就是教会的合一。他引用耶稣对彼得说的话:“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16:18,19)”。耶稣复活后也曾对彼得说:“牧养我的羊(马太福音21:16)”。虽然彼得是第一位得到赦罪权柄的人,但是复活后的耶稣也照样把这一权柄赐给了其他使徒。正如他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约翰福音20:21-23)”。所以,其他使徒与彼得一样领受了相同的权柄。彼得并不因为他是第一个从主领受赦罪权柄的人,他的地位就比其他使徒们更高。十二使徒从一位主领受了赦罪的权柄,所以他们乃始于一,源于一。正如耶稣所祷告的:“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二为一,像我们合二为一(约翰福音17:22)”。主既然赐给十二使徒相同的权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合二为一,所以,使徒的合一是源于一位主。既然源于一位主,相互之间就不应该存在高低或主次之分。正如保罗说:“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以弗所书4:4,5)”。如果使徒的合一是始于一位主的差派和吩咐,那么经过位分的传承所按立的主教也应该保持这种合一,每一个的主教不是各自持守各自的真理,而是每一个主教持守全部,一个真理必须被所有主教共同分享,即由一个主教团或主教职共同持守一个真理。正如西普里安说:
“这种合一我们应该坚持并且主张,尤其是我们在教会中作主教的,更应当如此行,好证明主教职本身是独一不分的。谁也不可用虚假欺骗弟兄;谁也不可用不忠实的遁辞败坏真道。主教职是一个,它的各部是由个人为全部而持守。教会也是一个,她由生养众多扩展普遍到四方成了群。[7]
使徒们因为同蒙一位主的差派,因此同有一个指望。主教们因为位分的传承,也同享一个真道。教会也是如此。教会既然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体,那么她也应该同有一个指望,同享一个真道。虽然教会在地上数量众多,但教会也是一个。[8] 西普里安使用许多比喻解释许多教会与一个教会的关系。他说:
“日头虽有许多光线,却只是一个光体;树木虽有许多枝子,却只有一个从坚韧的根里发出的力量;从一个充沛的水泉虽涌出许多支流,却只有一个源头,然而在源头里仍保存着合一”。[9]
所以,地上的教会好比光线和枝子,而那“一个教会”则是日头和树木。地上的教会是那“一个教会”放射出的光线,是那“一个教会”伸展出的枝条,也是那“一个教会”涌出的支流。她是所有地上教会的能量之源。他说:“倘若要把树枝折断,它就绝不能发芽;若把支流从源头断绝,它就必定干涸。教会也是如此,如果那“一个教会”与设立她的主隔绝了,教会也必然要衰亡。西普里安使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他把“一个教会”比喻为母亲,把地上的教会比喻成由她生养的儿女。另外,他也称这“一个教会”为基督的新妇。他将家庭的类比与婚姻的类比结合在一起,以从婚姻到家庭的自然秩序把基督与教会相连。不难理解,“一个教会”只有先作为基督的新妇,才能成为地上教会的母亲。好比一个没有新郎的新妇谈何生养并哺育她的后代呢?正如西普里安说:
“基督的新妇是不能淫乱的,她是端庄纯洁的。她只知道一个家庭;她用贞洁保守一个床榻的神圣。她替神保守我们”。[10]
西普里安力促教会的合一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为了教会合一在对待异端上未免有些矫枉过正。在文中,他指出异端不仅过去发生过,而且会继续发生;有些人随从己意在聚集之外的人间作领导者;擅取主教的名称;无视法规,自封为高级教士。他毫不客气的将这等人用圣经中的话形容为“恶人”,“糠”,“用舌头行欺骗的”,“用狡猾败坏真理的人”。可以理解,如果这一类人竟擅自分裂主的教会,肆意在教会间制造分门结党的事或者从恶毒的舌头吐死毒伤害人,我们确实应该不要听他们的话。正如西普里安说:“主大声反对这种人;他召呼他迷失之民离开这种人。”[11] 他还引用圣经上的话说:这些假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说话,但不是出于主的口(参耶利米书23:16-22)。”[12] 根据以上的陈述,如果教会遇到大分裂或者面临严峻挑战时,主教制的建立可以成为防卫真理及教义牢不可破的城墙。但是,似乎他的警告过于严重,导致教会内的异己之见可能也落得个遭到抵制和责备的下场。正如奥尔森说:“西普里安之后,基督教的主教职权,同时是咒诅与祝福。祝福,是因为他的合一能力;咒诅,是因为它会打击教会里的异义声音与个别信徒的主动精神”。[13] 但不管怎样,西普里安的合一观与当他当下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由于德修皇帝(Decius)的迫害(250-251),许多基督徒放弃信仰。后来在商讨如何对待这些人时,便产生了分歧。到底应该终止他们的信仰?还是令他们悔改,恢复信仰呢?正因为从中产生的分歧与不和,才有这篇《论教会合一》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只有当教会面临分裂瓦解之危亡关头,合一的重要性才显得完全必要。否则分裂教会就等于拒绝真理和救恩。没有真理和救恩就没有拯救和出路。因此,西普里安曾反复说,“人若没有以教会为母,就不可能以神为父”;“只有一个教会,教会之外无救恩”。可以说,当教会面临大灾难之际,主教制在免于教会妥协于其他福音的危险上意义重大,因为他可以有效的把真理保存在唯独教会可以采取的教导和诠释中,教会在基督真理释义上的高度主宰权并非是某种专制主义和霸权行径的独特彰显,只因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倘若教会与基督分离,教会在地上便失去了一切新约圣经启示中的神圣图像[14],如果基督作为唯一的拯救不能被教会有效的保存在唯独她才可以面对信众所开展的宣讲事工中,那么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在救恩方舟之外的沉没也必将导致教义学理解下的整个三位一体上帝信仰的彻底混乱。
对于今天的中国基督教来说,西普里安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主教制本身,更重的是他将主教制与救恩的教义巧妙的连接起来。从而确保教义可以获得行政意义上的权威性。然而,就中国基督教的特殊性来说,中国基督教已经进入“宗派已过”时期,并没有一种确定的教政制度作为中国教会在思想和管理上的具体体现。正如陈泽民教授说:“中国基督教的教会论是一个薄弱环节。不论在神学理论或实践上,主教制,长老制和公理制都适宜。[15] 王艾明博士也说:“由于中国教会在教义的解释上无法确定行政意义上的权威性,导致单纯的教义神学的结论无法真正形成类似与古公教会的主教会议或公会议所裁决的决议,来统一中国各地教会的思想和理解”。[16] 然而,笔者并不在此强调要将主教制作为一套优越的教政制度强加给中国教会,它唯一带给中国教会的启示和异象正是它以一种集体议事的模式让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的中国教会在我国现代化进程潮流中领悟民主精神在办好教会中所发挥出的重要作用。[17] 只有对民主意识的强调,才能断绝教会中仍尚存在的专制倾向,然而,民主意识在教会自身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不仅仅是圣职阶层相互之间的集体议事,也需要涉及支配整个教牧阶层决策取向之神学导引。正如王博士说:“教制与教规的创设首先是圣经观的选择,而一定圣经观的形成又是教会教义学基本规定的必然结果”。[18] 因此,凡有异端倾向的个人主张或集体立场,以及任何自大狂式或家长式的办教方针和神学导向都将在一种集体议事协商机制和教会教义学研究机制上完结。也正是对这两大机制的重视和强调确保了基督教的核心教义-救赎,在只属于教会可以给予其诠释和订正的绝对权威之中。
参考文献:
1.(美)奥尔森(Roger Olson)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美)胡斯都·L·冈察雷斯(Gonzalez, L.)著,《基督教思想史》,陈泽民,孙汉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
3.(英)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著:《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8年。
4.《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6年。
5.许志伟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6.陈泽民著:《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
7.王艾明著:《神学:教会在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1] 彼得从基督得到赦罪的权柄,然后通过使徒统绪的按立手续,传递给继承人,所以彼得从基督得到作第一位主教的权柄,并使教会团结合一,没有这种权柄就没有真理或救恩,透过时代的改变与位分的传承,主教的任命与教会的计划于此展开,并且教会的每个行动都在这些管理者的控制之下。参奥尔森(Roger Olson)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15页。
[2] 冈察雷斯(Gonzalez, L.)著,《基督教思想史-第一卷》,陈泽民,孙汉书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3] 西普里安主张联邦式的主教制(federated episcopacy),其中各位主教都有一定的自治权,虽然他还必须听取其他主教好友的意见,并且必须服从教会会议的决定。西普里安本人治理非洲教会的方法正体现了这种主教自治的主张。每当他必须作出可能影响到其他同工的决定时,他总是请他们来举行会议。同上,第233页。
[4] 这段话可能具体出自当罗马的主教司提反想要撤销西普里安在迦太基召开的主教会议所作的决议时,因西普里安完全不理他的宣告而产生的一段论述。参冈察雷斯(Gonzalez, L.)著,《基督教思想史-第一卷》,第233页;奥尔森(Roger Olson)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115页。
[5] 同上,第233页。
[6] 居普良,“论教会合一”,载《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6年,第300页。
[7] 同上,第301页。
[8] 全世界有不同教会的类型存在:圣公会、浸信会、信义宗、卫理公会、东正教、长老会、罗马天主教等等。虽然教会具有很多种类,但是依然可以找到促进不同种类的教会合一的根据。根据安提阿的伊格那丢之名言,“基督在那里,教会就在那里”。指出教会合一的基础为基督,而不是任何历史或文化的因素。在整个新约圣经中,地方教会的差异性并不会损及教会的合一。教会已经拥有一种合一,因为它同有上帝的呼召,而在不同的文化和情景中,它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从理论上说,教会只有一个,即一个以基督为基础的教会。西普里安也说:“教会被主的光照亮,就放射她的光线到全世界,然而分散到各处的是一个光,而全体的合一也并不被分离”。参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著,《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8年,第491-493页;参居普良,“论教会合一”,载《尼西亚前期教父选集》,第302页。
[9] 同上,第301页。
[10] 同上,第302页。
[11] 同上,第305页。
[12] 同上。
[13] 奥尔森(Roger Olson)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史》,第117页。
[14] 在新约圣经中,使徒保罗使用了三个图像来描绘教会。第一,教会是上帝的子民;第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最后,教会是圣灵的殿。参许志伟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
[15] 陈泽民,“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载陈泽民著,《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07年,第160页。
[16] 王艾明,“远象中的中国教会”,载王艾明著,《神学:教会在思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第411页。
[17] 从古公教会主教间的合作关系模式来看,主教们议事传统后来由于政治和历史因素在神治政体时代逐步丧失其最初的规定而演变成今日天主教梵蒂冈圣统制,而新教主流教会只逐步地以Synode(教会议会)的形式继承了古公教会的主教议事制传承。作为对教会权威性构成因素之一的教会领袖模式的分析,引申出的集体型领袖模式用意在于,对于今日中国教会来说,民主原则将作为中国教会治理的重要工作原则。同上,第306-307页。
[18] 同上,第311页。
(注:本文作者为北京一高校宗教学专业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