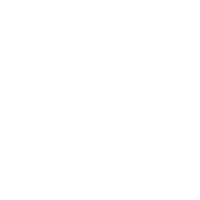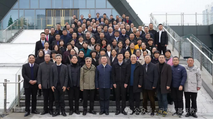从教义神学视野试论在类比基督教与儒家文化过程中应该把握的界限(上)
神学视野下的文化界限:三个类比
(一)儒家之“父子关系”与基督教之“父子关系”
海老名弹正[10] 接受基督信仰以后,除了一心侍奉上帝以外,也渴望基督教日本化。他试图通过将基督教与儒教类比(Analogy)的方式向生活在儒教世界中的日本人证明基督教的合理性。由于受到儒教五伦之道君臣、父子等伦理关系的影响,效忠君主、父子有亲的传统思想在海老名的意识中根深蒂固。自明治维新之后,海老名经历了一段君臣关系的真空时期,而正是基督教的上帝填补了他精神上的空白,为他找到了一位他可以永远侍奉的君主。
海老名从自己的宗教体验出发,以已为臣,以上帝为君,以儒教教导的君臣关系来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在他经验上帝的过程中,体验到己为子,上帝为父的父子关系也十分明显。但是,海老名以自己的宗教体验来建构他的神学或者说以儒教思想来解读基督教神学可能十分危险。在与植村正久的神学论战中,海老名将上帝与基督的关系理解为儒教语境中的父子关系。他认为,“在基督的意识里存在着与神在伦理上的父子有亲的关系”。[11]
也就是说基督作为子在表达与父的关系上时将儒教的孝悌精神作为人的榜样确立下来。人类的至善、人性的光辉可以在基督的生命中得到完美的表达。上帝与基督存在如同五伦关系中父与子一样的伦理实质。从本体论来说,为了避免尼西亚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和卡尔西顿公会议决议(Council of Chalcedon)的批评,海老名说:“基督是拥有神实质的神子,相对于神而言,他是人;相对于人而言,他是神。基督与圣父是同一本质”。[12] 但是他并不同意神成为人,即道成肉身的真理。他认为,耶稣是单纯的人,由于受到神的活力才变成神的儿子。[13]
由于父子有亲的儒教思想深深影响海老名的宗教意识,所以他的神学显然与传统的基督教神学不同。他把父子有亲理解为万物之理,贯穿于上帝与基督的关系以及人类的宗教意识中。耶稣作为一个普通的人,经由神的激励,将蕴含在世间万物中的普遍真理-父子有亲明朗化,并在与父的密切交往中将此真理表达到极致。因此,就之前在本体论的理解上,海老名只能接受就耶稣成为为神的儿子这一点上拥有与父相同的实质,而不能接受在太初基督与上帝同在的真理。可以说,海老名在类比儒教与圣经真理的积极探索中寻找到了父与子、上帝与基督在伦理实质上相类似的表达,但是因拒绝承认基督与上帝同等,从永恒生出并持续到永远。他的神学难免不会被贬为嗣子论。
植村正久的回应精准到位,他说,“基督与海老名的关系只不过是前后辈的关系,若此,基督便不再是拯救人间罪恶的救世主”。[14] 尽管海老名在表达了儒教的忠孝伦理这一点上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在类比两者的努力中不知觉的堕入从属说(Subordination)和嗣子论(Adoptionism)[15] 的圈套,这不但被大公会议决议被定为异端,对于理解十字架救赎的真理也没有益处。
(二)儒家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基督教之“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金规则在基督教的表达中是肯定性的。即“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路6:31;太7:12)。而在儒教思想中的表达则是否性的,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篇》)。耶稣说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而孔子则认为这是一句终身可以奉行的话。如果这两个原则用“爱人如己”来概括是否可以说它作为共同道德对人类具有普遍约束性又能被证明具有合理性?
根据梵里金的研究,金规则本身并不是共同道德而是作为一条实践智慧开辟了共同道德的前景。[16] 之所以金规则不能作为共同道德的一个原则是因为即使行动者和接受者的需要是相容的,也可能与合理的社会、道德规则相违背。如果行动者希望其他人以一种不道德的方式对待自己并从中获得快乐,那么他就应该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其他人。
或者说他把一种被社会普遍不接受的事物作为自己想要的事物加给别人。例如可能包含性虐待、同性恋、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等欲望和偏好。根据格维斯富有洞察力的分析:“规则所依据的这些“需要”或“欲望”包含着偶然性的偏好。假如“金规则”要成立,那么正当的标准必须与偶然性和潜在的任意性脱钩,否则将依附于被毫无保留的接纳的任何欲望”。[17] 也就是说,金规则只有根植于道德必然性中,它才有可能作为共同道德的一项原则,否则它带来的是道德上的毁灭。
从这一点来说,类比基督教的“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和儒教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存在哪一家的教导更为优越,因为它有可能被人类丑陋的欲望和偏好利用作为实践其个人标准的一条实践性原则。除非为此原则提供一个道德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以保证个人依据的标准不包含邪恶的动机。儒家的经典《论语》和基督教的经典《圣经》都包含了至今被普遍接受的伦理思想和道德观念。但如果从教义神学视野的角度去论证,到底那一套价值系统可以加强并保证行动者与接受者的需要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除了考察师徒之间,如孔子与子贡、耶稣与门徒们的对话为我们提供的道德范本外,还不能忽略超自然经验,然而这只在耶稣完成了对门徒在地上的训导之后才发生。
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事件为早期教会的门徒乃至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奠定了一个超越性的基础。正如德雷恩(John Drane)说:“上帝的灵在人的身上以一种不可理解的方式做工,赐给人们一种新的道德力量,使人们能够成为他想要他们成为的样子”。[18] 正是登山宝训与五旬节圣灵降临这前后形成的呼应性确保耶稣说的“爱人如己”和“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这两条道德原则可以顺利实施。而在孔子的训导体系中则找不到与之相呼应并保证道德实践的超越者存在。根据儒家的观点,人的良心就是道德价值的内在根源。
不过,在儒家的价值系统中也能找到一个形上学的名词—“天”,或者称“天道”。但这并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人格神,而是类似于康德的道德的形上学,“天道”通过良心得以彰显,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不像基督教的上帝与人类之间有一种活泼、明朗的、父子般的亲密关系。所以,在类比基督教和儒教的实践智慧时必须以整体而非局部的视野考察道德的根源问题。可能不同的源头领人走向不同的道路。
(三)儒家之“良心说”与基督教之“恩典论”
孟子有一句名言:“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我们没有经过学习而有的才能叫“才能”,没有经过考虑而知道的叫“良知”。也就是说“良心”或“良知是人与生俱来就有的”。加尔文认为上帝不仅赐予人理性,更有一个心灵的觉悟,直觉地感受到上帝的存在。加尔文称为“神圣意识”或“宗教的种子”。因为人有这种神圣的觉悟,可以解释为人类宗教的普遍性、人对神明的敬畏,以及人的良知与恻隐之心。[19] 正如孟子著名的思想“四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保罗也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2:14-15)。也就是说,“良心”、“良知”、“恻隐之心”或“是非之心”是人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一种价值判断或道德准绳。根据儒家的观点,良心是作为人道德判断的内在根源。还有一个超越的根源,儒家称为“天”或“天道”,但是非传统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及唐君毅共同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58年)明确表示:
西方一般之形上学,乃先以求了解此客观宇宙之究极的实在与一般的构造组织为目标的。而中国由孔孟至宋明儒之心性之学,则是人之道德实践的基础,同时是随人之道德生活之深度,而加深此学之深度的。这不是先固定的安置一心理行为或灵魂实体作物件,在外加以研究思索,亦不是为说明知识如何可能,而由此心性之学。
此心性之学中包含一形上学。然此形上学乃近乎康德所谓道德的形上学,是为道德实践之基础,亦由道德实践而证实的形上学。而非一般先假定一究竟实在存于客观宇宙,而据经验理性去推证之形上学。[20]
由此可见,儒家的天道观并不相信有一个现实世界以外超自然存在,更不会接受一个超越的存在是保证道德实践的基础。“天道”则是“道德的形而上本体”。以道德替代传统的形而上基础-上帝。道德具有普遍必然性,是人类可以普遍经验到的事实,是先天综合判断而不是超验的不可知的范畴。道德的根源就是“天道”或“良心”。虽然一个是内在根源,另一个是超越根源,但是并非两个独立的存在,而是彼此相通的。或者说“良心”和“天道”本就是一体。“良心”反映“天道”,“天道”启发“良心”。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
“良心”其实也可以和“仁”联系在一起。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就是说同情心是施行“仁”的开始。“仁”在儒家的“五常”中居首位,其次是“义”、“礼”、“智”、“信”。在孟子的“四端说”也中也排在第一位。“仁”通俗的说就是同情人、爱人、关心人,让天下所有人都安居乐业,是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古语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说:有志者不可以不培养坚强的意志,因为责任重大而且道路遥远.以实现仁德为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为此理想奋斗终身,这样的道路不是很遥远吗?
还有一句话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篇》)。意思是说:“志士仁人,不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只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21] 综上所述,“良心”、“仁德”是中国贤达之士追求的最高境界。但是此境界并不是依靠外来的启示或者救恩获得,而是依靠自己的顿悟和实践。正如《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
此中我们必须依靠觉悟而生实践,以实践而更增觉悟。知行两者相依而进。···但此觉悟,则纯是内在于人自己的···人性即天性,人德即天德,人之尽性成德之事,皆所以赞天地之化育。[22]
简言之,人就是上帝,人自己就是自己的道德指南,无需一套外来的启示或真理为人类提供指引和方向,乐观相信道德全凭觉悟,觉悟道德就要实践道德,在实践道德的过程中又觉悟道德。但是,如果说人的本性是软弱的,根本无力觉悟和实践道德并且这就是人的本相会如何呢?中国文化高估人的价值,但是《圣经》却一语道出人良心的全然败坏。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我真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7:18-24)?
在保罗看来,纵使他渴望行善,但是他的本性中没有力量将之化为行动。他发觉在他的生命中总是有一个律在起作用,使他所有良善的试图均已失败告终,想要行良善的事,却总是犯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说:“虽然我身为修士,生活无懈可击,但是我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在神面前良心不安”。[23]早在公元五世纪初,因“自由意志”问题爆发了伯拉纠(Pelagius)与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之间的争论。
伯拉纠高举人类的自由意志,认为人可以做上帝所要求的美善的事,上帝颁布的所有道德命令都是人可以遵从的,因为在人性中先天就有向往美善和福乐的倾向,当人犯了罪以后,必会为自己所犯的罪负责,自动转向罪的对立面,从而修正从前的错误。
而奥古斯丁则持人性是软弱的立场,奥古斯丁相信人虽然有自由意志,但这自由意志已经受到罪的捆绑,不能自主做出全然美善的决定,如果要是自由意志能趋善避恶,必须要借助一个外在力量的介入,即上帝恩典的医治,那么被损坏的自由意志才能得到修复。根据基督教神学,将人深陷罪的窘境描述为“全然败坏”,但是此教义并不否定人类社会没有良善可言,这不符合人类的经验事实。相反,还处处可见爱国守法、光明磊落、公正廉洁的美好品质。许志伟博士说:“不少没有基督信仰的人亦做了大量济世为怀的善行与使人钦佩的行为,其大公无私的胸怀往往为基督徒所不及,基督教神学相信这些善行反映了上帝安置在人心的一种普遍恩典”。[24]
即神对所有人的爱和祝福。但是普遍恩典不足以使人脱离罪的权势,除非有上帝十字架恩典(特殊恩典)的介入,人才会真正爱人和爱上帝。所以,良心是不可靠的。保罗说:“有人离弃真道···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提前4:2)。“他们离弃真道,以自我为中心,渐渐地他们的心就对真理变得麻木、漠不关心。如同皮肤因为习惯了高热的温度,皮肤长出厚厚的老茧,对于高温就不再有什么感觉了”。[25]
总的来说,儒家强调的内在超越,以心为镜,通过自己的觉悟和实践向“仁”的境界迈进。基督教强调的是外在超越,承认自己里面没有良善,全然寻求一位超越的上帝,以上帝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己心,领导己心。以信心出发,建立价值根源。邓启耀博士说:“儒家的‘心源’”若没有连于圣经启示的‘圣源’就会越走越窄,步入穷巷”。[26]
笔者认为,中国文化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经过精心描绘的宏伟蓝图,虽然图纸上展示的工程浩大雄伟、美轮美奂,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却因债务纠纷、违法违规,以至于建造的工程残破不全,甚至停工整顿。这就回到了保罗自白中的叹息,不是我想不想、知不知的问题,而是我能不能、行不行的问题。虽然儒家和基督教都强调道德,但是实践道德价值的前提不同。
儒家以人性、良心作为道德实践的前提,而保罗则以称义和成圣作为基督徒生活守则的先决条件。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新约学者认为罗马书不能只从12章读起,如果忽略了1-11章,第12章的讲论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基督教伦理与别的宗教伦理最大的不同。
别的宗教是以行为开始的,但保罗的伦理却是以神为中心,以基督为依靠,一切从救恩说起。伦理是因救恩而起而不是因行为而起。伦理不能没有救恩而独立存在,没有在基督里被称为义的身份,便没有可能实践基督的伦理。
叁 结语
综合以上的思考,这就迫使我们要去思想神学的本质和任务。只有神学健康且充满活力,它才能担任起批判教会、归正教会的职责。教会作为一个在现世中以彰显上帝国度为导引存在的属灵群体,必须以释放受压制的生命,使受捆绑的心灵得自由,让上帝的律法在人的心灵中作王掌权作为其基本特征。如果教会失去上帝赋予其独有的自信,反而因不能与世俗学问接轨而自卑哀叹,教会必然走向没落。
余达心博士(Carver Yu)有一段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说:“无所用的神学为继续求存,往往会出卖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变身,无求得世俗之学的尊重,能以保留其在学术殿堂中小小的角落,结果为世俗之学所俘虏,化为宗教研究之学,视教会历代的信仰为尴尬,不惜以文化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及各形各式的意识形态把基督教信仰去上帝化、去基督化,重新诠释信仰,务求将世俗的排拒降至最低,以致他能与世俗之学同游”。[27]
中国传统文化固然有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态度的一面,在二十一世纪硬实力发达,而软实力相对落后的中国提倡国民阅读经典稀释浮躁之心更是理所当然之事。基督教会既然在中国得以建立和开拓,就应该尊重当地文化,但是尊重不意味着妥协。这种妥协是以牺牲十字架救赎的真理为代价,将真理与文化等同,将神学与国学并列。
如果说这种举动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让在儒教教育环境中成长的中国人更能理解基督真理就如同海老名以儒教与基督教类比的方式让生活在儒教世界中的日本人也觉得基督教的真理也是很恰当的这一个目的,虽然因此而赢得某一个文化处境的认可但若落得个基督教与文化都是与人向善的人文主义或宗教学见解而没有因受救赎思维的引导和牵制产生的个体的生命转变绝对是得不偿失的。斯托得(John Stott)说:“基督教是一个拯救的宗教,它的信息是传讲一位顾惜罪人,又为罪人而死的神。这信息,在世界其他宗教上独树一帜”。[28]
教会牧者只看到基督教的人性、道德的层面是肤浅的,还应当把握整本圣经是围绕“救赎”展开叙述的。从亚伯拉罕蒙召走出吾珥,到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再到先知以从神来的启示教导以色列人等无不是指向耶稣基督的救赎。出埃及、逃脱巴比伦、先知的呐喊教诲都预表了将来的那一位要将人从罪恶的奴役和捆绑中拯救出来并且要成全历史上众先知期盼以色列民回转后所表现出的生命样式。上帝晓瑜耶利米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9页。
[20] 邓启耀(Kai Tang)著:《良心可会比天高-圣经真理如何超越中国文化》,列治文:道世基督使团,2009年,第32页。
[21] 杨伯峻译注:《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8页。
[22] 同上,第34页。
[23] 麦葛福(Alister E. McGrath)著:《基督教神学手册》,刘良淑,王瑞琦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第445页。
[24] 许志伟著:《基督教神学思想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55页。
[25] 邓启耀(Kai Tang)著:《良心可会比天高-圣经真理如何超越中国文化》,列治文:道世基督使团,2009年,第37页。
[26] 同上,第38页。
[27] 余达心(Carver Yu)著:《聆听:神学言说的开端》,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14年,第20页。
[28] 约翰·斯托得(John Stott)著:《真理的探索-基督教是否可信》,谢志伟译,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2015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