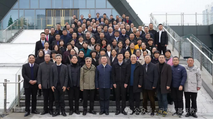从记事起,我与外公生活的日子加起来也仅仅是两三年的时间,但他的生命品行、他的坚定信念却深入骨髓般地影响了我。
下面这段记录,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如故事,在耳边听过;如电影,在眼前放映;到如今,刻在心里,留下深深的烙印。

我的外公潘仰贵牧师(1904.2-1986.3.),字颂卿,解放前在山西临汾教会服侍,山西洪洞男道学院上学,上海江湾神学院读神学,后在京(北京远东宣教会)、津(天津大直沽教会)、冀(张家口教会)、蒙、绥地区传道,上世纪五十年代任山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委员,山西省临汾县(后改为临汾市)政协委员,离世前是山西省临汾市基督教会牧师。
印象中的外公高大魁梧,声音洪亮,留着一把山羊胡子,儿时我们姐妹三人都曾围坐在外公身边,为他梳过长长的胡须,后来外公拄上了拐杖,看着背有些驼了,但他的腰板仍挺得笔直。
如饥似渴慕主道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清政府日薄西山,统治风雨飘摇,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侵华,签订不平等条约……内忧外患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904年2月28日外公出生,生于山西省临汾市尧都区金殿镇小榆村。临汾位于晋西南地区,又称“尧都平阳”,因地处汾河之滨,是产粮区,若没有战乱、遇风调雨顺的好年份,村里人只要有土地可以勉强糊口过日子。当时平阳地区很多人家都种着大麻,许多人因吸食大麻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年主的仆人席胜魔(1835-1896)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接受福音、悔改传道,成为晋南临汾第一位牧师,他开办的戒烟所和他的服侍影响深远。
时年,我外公的父亲潘登嬴,系清朝末年的一名武秀才,身怀绝技、性情豪爽、扶危济贫,因着年轻气盛与人发生口角,对方持铁锹向他劈打,他敌挡防卫时,铁锹回弹在对方头上致死,被县衙治罪投入大牢。家里人为保全其性命,变卖土地、倾家荡产把他从狱中赎回,从此家境败落。外公的母亲病故,他的哥哥过继给本族亲戚,他的妹妹为活命很小就嫁人,最后,五口之家只剩下外公和他的父亲二人艰难度日。
外公十岁左右就上山砍柴,背到城里去卖,有时也给人家打短工。一次,外公进城卖完柴,他看到一群人在一间学堂读书、写字,顿时心生羡慕。外公十五岁那一年(1919年),他鼓足勇气走进去,那是由英国内地会建立的临汾教会,他看到里面的人与他生活中的人不一样,这些人一个个脸上都带着平和与喜乐,使当时不断失去亲人、又活在贫困穷苦中的外公立刻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欢喜和满足,他悄悄坐下来,在一旁认真地听,跟着学唱,久久都不愿离开。
自那之后,每一天干完活、或卖完柴,外公第一件事就是要跑到教堂听道、学诗。时间长了,教会管事务的长者记住了这个少年人,交谈间又了解到外公家中发生这么多变故,于是把他留了下来,安排他在教会打杂,这样外公还没有信主,就进入教会,开始了在教会的生活和服侍。
外公主要负责打扫教堂内外的卫生、按时间摇铃,做教会的一切杂务事。他一边认真地作工,一边识字、读经、慕道,期间,他完全接受了基督的福音,并领受洗礼。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也都非常喜欢这样一位好弟兄,当时杨绍唐牧师(1898年-1969年,山西曲沃人)常在临汾地区传道,他看到外公既年轻、又渴慕学习主道,教会服侍也认真踏实,就起意培养外公,常常带领他读圣经,也带着他外出布道,那时的外公越来越愿意在主真理中追求。
1922年,临汾教会推荐外公到洪洞玉峰山男道学院学习,外公更加勤奋努力,毕业后留校作了一名教师。以后,临汾教会收到杨绍唐牧师写给教会的来信,极力推荐外公到上海江湾神学院学习。外公因家中贫穷,他的父亲无法供给他出远门的路费,更不舍得让心爱的儿子离开,于是竭力反对外公出去求学,外公为此切切祈祷,求神给他预备上学的道路。神感动临汾教会众弟兄姊妹为他凑了十块大洋。
1927年,正是战火纷飞、北阀混战之际,乡下老百姓都不敢出门,外公穿一件旧棉袍子,背着干粮袋子,辞别父亲,踏上求学之路。从家乡走出来时,外公根本不知道上海在哪里,但他说:“我有神的带领,有神的看顾,我的鼻子底下有嘴,难道还怕找不到上海吗”!外公沿着铁道线出发了。
当时火车沿线都是山西军阀闫锡山部队的士兵拉运军火,外公搭火车与士兵们一起前行,一路上他帮助搬运货物,清扫车厢,若火车停止行驶,他就继续步行,到大路上寻找可搭乘的车辆,一路上风餐露宿。在行程中,外公偶遇一位好心人,他得知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还有人不远千里去上海求学,这位素不相识之人竟主动给了外公几十元大洋,外公说:是神迹!以后的路途虽充满艰辛却也是恩典相随。
外公过了黄河,途径河南、湖北,在汉口乘船,又前往安徽、江苏,长途跋涉、千辛万苦,走走停停,三个多月的时间抵达上海,又步行几十华里找到江湾神学院。
站在神学院门口的外公,身上衣衫褴褛、囊中所剩无几,看门房的把外公当成了乞丐,外公赶紧拿出杨绍堂牧师的信,学校接待了外公,但上学需要支付二百大洋的学费,外公说:“我有的是力气、我可以干活”,就这样,外公因着有杨牧师的力荐,又以勤工俭学(作一名打钟员),被学校破例收取,他的室友和其他老师、同学知道外公的求学经历,也伸手帮助他,有的送衣、有的送鞋袜……1928年至1930年,外公在江湾神学院接受真理的学习装备三年,他对主道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更坚定了为主奉献的心志,因着外公学习成绩优良,神学毕业后被推荐到了北京前门远东宣教会(内地会在北京的教会)工作。
满腔热情侍教会
1932年夏天,外公将山西省杏花岭博爱医院(教会医院)作护士的外婆接到北京完婚。
我的外婆名叫维善良(1910-1979.8.),出生于山西河津一农民家庭,因着是家中第九个孩子,又是女婴,家人生活所迫,把她用布包裹起来、放在村头汾河边,并用小树枝盖着(当时她的亲人在不远处藏着、看着,如圣经中米利暗在芦苇丛看弟弟摩西)。那天正是礼拜天,一位老姊妹在去往教会的路上,听到婴儿的啼哭声,捡起送到黄村教会的李执事家中。
当年英国内地会在山西各地建立教会,有许多英国传教士在山西乡村服侍。当时有英国吉斯廷牧师夫妇正在河津一带的教会传道,他们曾经得到一笔钱,是英国一位姓维的女教习的爱心奉献,她希望在中国收养一名孤儿,并供养到大学毕业,当吉牧师夫妇在教会看到这个捡回来的婴孩,知道这是神的预备。这样,外婆被吉牧师夫妇收养,按那位奉献之人的姓起名叫维善良,外婆先被送到教会孤儿院,稍大后吉牧师夫妇就将外婆带在他们身边,有一次吉师母在新绛稷山传道的路途中翻车,摔断了腿要去北京看病,就把外婆寄养在教会柴(蔡)执事家中,因着他们家人把又瘦又小的外婆当丫头使唤苦待,教会一位好心的老姊妹就将外婆接到自己家中,并轮流住在不同的姊妹家里。
外婆自小在教会的环境中长大,又在英国传教士夫妇身边生活,深受他们信仰的栽培,特别是吉牧师夫妇的影响,外婆的信仰纯正,自小在教会长大,会弹琴、唱诗,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外婆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十几岁时,外婆被吉牧师夫妇送到霍县女道学院学习,在一次道学院的聚会中,外公、外婆二人相识,并相爱。当外公在上海江湾神学院学习期间,外婆被吉牧师夫妇带到省城太原,在教会博爱医院作了一名护士。
1932年,外公与外婆二人在北京远东宣教会完婚,那时的外公穿着长袍,带着礼帽,外婆穿着白色的旗袍(我的妈妈和舅舅都见过他们的结婚照),他们的婚礼得到当时教会牧师和众弟兄姊妹的祝福。1934年8月,外公外婆第一个孩子出生,起名贞德(圣经名字叫利百加,我的母亲),母亲其后有两个妹妹出生,但因着出麻疹相继夭折。那时外公外婆与北京远东宣教会的周维同牧师、王明道牧师和一位刘牧师都住在教会,他与当时的几位牧师一同热情地传福音、在街头开布道会,外公的属灵生命在教会的服事中日渐成熟。
教会一位席老弟兄听了外公的讲道很受感动,便与外公说起自己的一桩心事:他有一个儿子因不听话犯事被下在监狱,希望我外公能为他祷告。外公不仅祈祷,还到监狱探望,并给他儿子传道,一段时间后,那个儿子痛哭流涕,决心痛改前非。外公就把这一喜讯告诉其父,老弟兄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啊!便把儿子保释出来了,这位悔改归回的浪子后来领洗,还跟着外公到街上布道。席老出于感恩,把外公带到他的字画店里,说:你想要哪幅画,随便挑,我送你的。外公笑笑说:感谢上帝,我什么也不需要。席老硬是塞给外公一幅画,后来外公一家五口在天津遭了水灾,生活了无着落,才想起这幅画,拿到市上竟换回来了一百现大洋,解了燃眉之急,全家经历耶和华神的预备。
解放前的中国教会没有自主权,当时与外公在教会侍奉和生活在一起的有中国传道人,也有外国传教士,有一些外国传教士轻看中国人、也排挤中国传道人。有的外国牧师根本不尊重中国同工,包括一些生活小节,西方人用小盘、小碗、小碟、刀叉吃饭,看到中国人用大盘大碗就会取笑,外公性格比较耿直,有几次外公实在听不下去,就与据理力争,那时的外公也是年轻气盛,就义正言辞地告诉那个英国默克牧师:“你再侮辱我们中国人,我就拔你的胡子”……当时中国的教会把持在外国人的手中。从此之后外公在教会受到不公待遇,并且他们一再说:“你这个潘仰贵不适合在教会工作”,并想方设法排挤他,还通知内地会的教会不再聘用外公,这样外公被迫离开北京教会。
1938年-1940年间,中国华北地区正是抗战主战场,到处兵荒马乱,外公携家眷在察哈尔、绥远(今内蒙、山西大同)一带传道,1939年11月,外公外婆的长子在察哈尔出生,起名洪德(圣经名字撒母耳,我的大舅)。
1940年-1941年间,外公一家住在天津法租界大直沽,在那里的教会服侍。1941年夏,天津海河发大水,那年7月18日外公外婆的第二个儿子出生,外婆怀抱着出生刚刚七天的婴孩,坐着木筏子逃出来,由此给这个孩子起名叫摩西(从水中拉出来的意思)。外公带着一家人返回北京,暂居在一位同族亲戚潘姊妹的家中,不久与张家口同工取得联系,他们都欢迎外公到那里服侍,这样外公携带一家五口前往张家口。
在张家口教会,作牧师的外公继续讲道,外婆维善良与后来回到太原教会的张玉叶、韩妙英两位姊妹一起负责教习工作,外婆带着主日学。
期间,外公收到家书,说家中父亲有病,盼儿速归。这样,外公携带着家眷从张家口返回自己的家乡,回到起初蒙召、求学和奉献的地方临汾教会(回到临汾后外公一家留下一张珍贵的合影,成为我们家保存下来最老的照片1943年3月28日)

拳拳之心爱家国
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那时,日本侵略者早已侵入华北腹地,临汾平阳地区因着地理位置的险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山西临汾作为军事重镇,已经被日本人占领。1942年,外公全家从张家口回到家乡临汾,外公继续在教会服侍。
母亲当年不满十岁,童年时经历那一段被日寇践踏蹂躏的岁月,中国老百姓蒙羞受辱、担惊受怕的日子,每次提及,母亲都记忆犹新,说:只要有人喊一声:“日本人来了”,顿时一片混乱,到处鸡飞狗跳,人们都是能跑就跑、能躲就躲、能藏就藏。有一次,听说日本人来了,有很多人都涌进教会,寻找藏身之处,当时外婆紧搂着三个孩子、还有家里养的一只老母鸡,藏在家里东房的一个桌子下面,被涌进来的人挤在桌子下的角落里,屏着呼吸、不敢出声,过了好长时间,后来有人喊着:日本人走了。大家都松了口气,从桌子下来爬出来,从房间里走出来,这时,家里的那只母鸡也抖抖身子、撑撑翅膀、挺胸昂首,从房间轻跳着出来,当时惊魂未定的人们看着此情此景,都久违地笑了,这是在战乱中给母亲留下最深的一个画面。
作为牧师的外公原本想着返回家乡服侍父老乡亲和弟兄姊妹,但因着日本人的侵略,在兵荒马乱中教会不能正常聚会、牧师也不能讲道,很多逃荒的难民涌向教会。于是,外公在临汾教会成立“难民救济所”(百度可查),专门收留难民、安置难民,先后收留保护难民千人,这些人多是从河南、河北、安徽等地逃荒来的人,也有周围村中的穷苦人,外公就安排他们中间有气有力、身体较好的,为教会善胜医院清洗医院用品、医生大褂,作一些服务性的劳动维持基本的生活,大家都是吃住在教会。
不久之后,日本人完全侵占教会,临汾教会的礼拜堂成了日本军人的电影院。因当时外公在教会众弟兄姊妹中与众父老乡亲中有很高的威望,日本人就以各种利益诱惑外公,并要求外公作新民会会长(汉奸),若不答应他们,就下令立刻撵出教会。当时日本人限令下来,外公与外婆共同商量:“我们中国人决不给日本人做事”!于是外公做好全家搬出教会的准备,次日,日本人再次威逼利诱时,刚正不阿的外公坚定地回复他们,说:“我当不了你们的新民会会长,我也不愿给你们日本人做事”。随即,外公携带家眷再次被迫离开心爱的教会。这期间,教会也有的人选择为日本人做事。
外公一家搬到临汾贡院街一民房居住,一家人没有任何收入,从此之后,外公以自己的诚信向药房(太和西药房)赊药,背着药箱奔走在乡下村里,以卖药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期间,神也感动河西地区一些弟兄姊妹送来杂粮和面,使外公一家在艰难的岁月里得着供应。
外公背着药箱、带着圣经,步行走遍晋南襄汾、闻喜、绛县、稷山、河津等地,他一面卖药,一面传福音,随走随传。在这期间,外公两次遭到日本兵抓捕,一次被打得遍体鳞伤,致右腿膝部骨伤,在弟兄姊妹的帮助下幸免于难。外公也藉着卖药帮扶乡里乡亲和贫穷的人,常是拿出去药却没有收回钱。
我的母亲讲到,有一次吃饭时间已过了,锅里的水一直在火上煮沸着,家中没有一粒粮食下锅,她与弟弟都喊着肚子饿,外婆就带着他们姐弟三人一同跪在地上,对着灶台上的空锅做谢饭祈祷,这时听到有人敲门,来人说,他前些时候拿了外公卖的药,当时家里没有钱,现在地里收了一些黄豆,就赶快送过来了。
母亲说:那时我的外公常在外,外婆带着他们姐弟三人,“动不动就跪下来祷告”。当外公外出回来时,总是从他的干粮袋里变戏法式的拿出核桃、枣,带给他们姐弟们童年的快乐。
那时,外公外婆一家的生活常是在极度穷乏中,却又经历着神奇妙丰盛的供应,期间,外公相继在汾城县东坡堡教会事奉,闻喜教会服事,外公跑遍了曲沃、侯马、安邑、夏县、临猗……晋南几十个县,所到之处都留下外公传福音佳美的脚踪。
1945年8月,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内又开始三年内战,因着局势动荡不安,外婆带着四个孩子再次返回临汾小榆村居住,外公也由外县传道返回家乡。1947年,众弟兄姊妹听说外公已经返回,于是邀请外公主持教会内外的各项事务,外公重新开始在临汾教会服侍,全面负责教会的事工。
当时临汾教会各项事工有待重整,教会分南院北院,大礼拜堂能容纳两千人。同一时期临汾教会乔知己牧师也在负责教会工作,因为战乱,他离开临汾去了上海女儿那里。当时,教会接管善胜医院(由英国内地会建立,解放后为临汾专医院),外公出任善胜医院董事长,期间两次赴京、并两地空运回美国救济总署配给医院的大量药品和物资。当时善胜医院郝子刚(幹)任院长,王子清是长老,还有大、小王大夫,贾敬夫、马步清大夫等,护士有刘宝全、吕晋一、郭宝珍等,外公带领着教会众弟兄姊妹和善胜医院员工都积极参与救治伤病员。
1947年春,人民解放军在徐向前元帅的指挥下兵临临汾城。1947年末,母亲所上的临汾女师学校停课,因着伤病员剧增,母亲在善胜医院当了几个月的护士,帮助救治伤员。母亲回忆说:善胜医院所有的药品都是由太原红十字会美国救济总署供给,一次太原通知有一批药品和救济衣服要人去领取,外公就安排善胜医院的郝子刚院长坐飞机领回物资,当救济物品运抵后,外公跟外婆和孩子们说:咱们家的人谁也不能挤着去领取那些衣服和用品。我的母亲说:我们姐弟几个人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领走物品,也有人让我们去领,我们摇着头、摆手说:“爸爸不让领”……
1948年3月开始,临汾保卫战役72天,城内的国民党军作最后的挣扎和抵抗,他们任命外公为教会和医院的联防负责人,要求把水缸埋到地下几米深,安排60岁以下、12岁以上的大人小孩,每天晚上在水缸那里听动静,听见有挖土的声音就立刻报告。
1948年5月16日临汾解放前夜,炮火连天、硝烟四起,外公家房上住着机枪连,房背后是炮阵地,屋内是国民党官兵,大炮在头顶上轰轰飞,子弹在眼前冒火花,天空都被照亮、染红。那天夜里,外婆带着几个孩子和在教会中的一些弟兄姊妹瑟瑟发抖地躲藏在教会旁边的地洞里,一晚上都是炮轰的声音,随着一声震天响,城墙被炸开了,听到嘹亮的军号,解放军进入临汾城。
那一夜晚,外公和教会医院负责人和一些同工在开董事会,他们都藏在善胜医院的地洞里,一夜的炮轰过后,17日清晨,解放军进入城内,外公带着一位已经信主的国民党军官赵茂轩,一同迎接解放军,外公带领着解放军首领直抵西门西关敌军司令部。其后,外公又返回教会,教堂和居住的房屋在炮火中都烧毁了,外公见此情景,又见不到一位亲人,伤恸至极、失声痛哭。
那时,外婆带着五个孩子(外婆怀中抱着8个月的小儿子(我的小舅),我的母亲背着她的三弟恩德,她的大弟洪德拉着二弟福德),还有曲沃的两个姊妹、两个受伤的国民党士兵已从地洞出来,一家人看到教堂和家全都烧没了,就随着难民先往西跑,一路上被倒在地上的死人绊着,实在无处可逃,外婆就带着孩子们跑到善胜医院大厅前避难,那时有许多的难民和病人全挤在医院大厅的药房桌子底下、柜子旁边,一个孕妇踉踉跄跄把母亲和弟弟他们挤到一边,叫喊着肚子痛,倒在地上随即地上染成红色……
外公在教会的废墟上呼喊着、悲痛焦急地寻找着家人,一位解放军军官告诉外公,他看到有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往医院方向去了。外公立即返回善胜医院,在大厅看到一家人尽都平安,抱着孩子们又是喜极而泣,颤抖的双手摸着每一个孩子的脸,喃喃地说:“都活着,都活着!活着,就是万幸,活着,就好”,外公举起双手献上祈祷:“主啊,我感谢你!在炸弹满天飞的夜里,我的家人都毫发未损,感谢全能的阿爸父神……”,外公安抚、安顿家人之后,立刻去又去察看医院和教会。
教会这次损毁严重,五间房屋全部烧毁,北院和教堂成了一片废墟,只留有南院几排房子,大礼拜堂的钢琴被烧毁(大舅那时9岁,清楚记得在教堂的院子里捡到钢琴内的铜簧片吹着玩耍),外公一家在教会里所有的物品全部烧了,外公顾不上安顿自己的家,和另一位管理教会事务的翟风格弟兄(教会会计)一起,带着众人赶快收拾出南院三间房子作为礼拜堂,很多的弟兄姊妹也陆陆续续来到教会,有的帮助收拾院子,有的跑回家送来被子、褥子、锅碗,也有的拿来杂粮面和豆子,众人齐心协力,外公带领着众弟兄姊妹在满目疮痍的教会重新开始了聚会和敬拜生活。
新中国成立前,吴耀宗先生给临汾教会的外公来信,讲到外国人很快要回国,因教会的地契全部都在内地会总会,让外公到南京将教会房屋地契要回去。外公立刻起身前往南京,一路艰辛,历时一个多月,用麻袋扛回临汾教会三百多间房屋的地契,后又着手核对教会的房屋教产,有:北青狮子口的何二胡同,鼓楼东大街金埔安诊所旁、何家圈门等等,当时有很多人都取笑外公,去了趟南京背了一摞子麻纸回来,外公却说:这是临汾教会的命根子,是神家里的产业。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9月23日,由吴耀宗先生等40多位基督徒代表发起,《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后称“三自宣言”),由此开始中国基督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道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基督教会相继成立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外公是山西省基督教三自爱委会发起人之一,任山西省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晋南三十八县的执行常委,临汾县(20世纪80年代改为临汾市)政协委员。
解放后,外公继续在晋南地区传道。因临汾教会个别人对外公的非议,1953年外公到洪洞教会服侍。临走时,买了三个大火柴箱收拾家中的行李,弟兄们都劝说:潘牧师啊,你就把教会的几个大铁箱子拿上用吧,外公说:“教会的东西,我一点儿都不能拿”。
那些年日,外公和所有中国人一样经历了天灾、人祸,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外公仍充满信心,1960年外公给山西省医学院上大一的次子(我的二舅)写信:“你要安心学医,为人民、为祖国,为人类服务”。

在文革时期,因着外婆有海外关系(英国夫妇收养的女儿),因着外公的牧师身份,随时面临批斗挨整,当时我三舅和小舅在乡下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小舅是老三届,准备考大学之日正值文革开始,只好在乡下务农,当时十八九岁的小舅能写会唱,公社和大队排戏、演戏都叫他,写材料、写大字报都是他执笔,这样他会了解、知晓一些内幕,外公外婆因提前得到消息就避开了各等的迫害,小舅说:“要不是我让他们躲起来,你外公外婆早就被整死了”,感恩神用这种奇妙的方法保护了外公外婆的性命。1970年,母亲怀着八个月的我回到娘家临汾小榆村待产,我在外公外婆的祈祷中平安来到人间。
那个年代的外公脸庞清瘦、文质彬彬,戴着一付眼镜,每天早晨天未亮就背着背篓,到乡间小路或公路上去拾粪,他拾的粪在门口堆成一座小山包。当年因着外公外婆的特殊身份,所有儿女在家庭成份一栏都写着:宗教职业者,五个儿女带着这个特殊的身份,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至工作都受到极大影响。
文革时,我的母亲和舅舅们因担惊受怕,把家中的圣经、所有外婆与英国传教士的照片、以及外公在北京、天津教会的照片都付之一炬,后来想起来都是遗憾。
1978年,改革开放似一声春雷,带来教会的春天。全国各地的教会相继复堂开始聚会。此时的外公已是古稀之年,他仍外出讲道、看望弟兄姊妹,曾多次来省城太原住在我们家里,我还记得他在教会过圣诞节时给我们带回花生和糖,外公也在太原北营地区的郑村等地传道。
外公一生清贫,生活极其简朴,我记忆中外公一日三餐就是棒子面馍就着辣椒,以后生活好些了,是白面馍馍就辣椒,这也是晋南人特有的饮食习惯。外公的外形高大魁梧,内里却有着一颗柔软的心肠,他怜悯穷人,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施比受更为有福”!
外公在太原与我们同住的时间,常带着我和姐姐、妹妹端着铝饭盒,给周围捡破烂的一家人送肉、送吃的,那时我的哥哥刚刚在肉联厂上班,家中可以吃到相对充足的肉。外公从家里出门时,母亲都会给他一些零钱,但外公无论多远、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拄着拐棍走回来,因为在回家之前他已将身上所有的钱一分不剩地给了他看到的有需要的人。
1986年3月10日,82岁的外公在所有儿女们的陪伴中,含笑归回天家。离世之时,没有留下分文,唯一留下的是他使用过的一本繁体字、竖排板的圣经,用蓝色布包裹着,里面写满了外公读经所作的标注。如今,我只要想到外公,就想到他在我们家的一间小屋里跪在床头祈祷,坐在床上唱诗,戴着老花镜读圣经,用纸卷起来的油笔芯在圣经上作笔记;只要想到外公,我就想到他带着荣光的脸,他微驼的背,却又挺直的腰板,这些不仅浮现在我眼前,更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外公数次离开心爱的教会,有被迫与无奈、有心碎与忧伤,但我更看到一个带着满腔热血、一身正气的中国人,为赢得民族自尊而拒理力争;我更看到一个刚直不阿、有着铮铮铁骨,却又普普通通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在腥风血雨中不畏强权的爱国情怀。
回顾这段历史,我为外公在神的手中被使用、在神的教会尽忠心,在家国危难之时,一名微不足道的传道人的大义凛然而感动不已!
如今,我追随外公的脚踪,承继他奉献的心愿,在西北基层教会作了牧师。在伟大祖国繁荣昌盛、日益强大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再蒙羞受辱,我们处身的时代不再混乱艰难,唯感谢主恩,赐给我们一个大好的新时代!
纵观千年教会历史,多少人事都已尘埃落定,多少生命都已如飞而去,但上主在祂所建立的教会、拣选的仆人和使女身上的计划和美意,永不更改。我祈愿:在每一个时代,主兴起合用的仆人,使用每一个宝贵的器皿,成为这时代的明灯,行在光中!
(本文作者现任新疆乌鲁木齐教会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