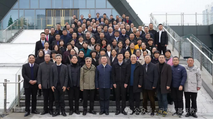我住北京多年,老公与我愈老愈爱到郊外小山村,种菜或种花,看书或画画,在园里营山造水,吐吐废气吸吸原气。远离家门口约五百公尺,还有一个教堂,教堂上有十字架,多年来它给小区居民生活之灯添了心油,犹如神在小区温暖体贴我们,教堂直到疫情才暂缓,许多弟兄姐妺总觉小区少了活动犹如“缺了柴,火就熄灭”(箴26:20)。
我家住这小区不止十年,与吴叔叔夫妇及吴姑姑毗邻多年,他们家的山楂总在我们家采,我们家的南瓜总爬到他们家结,两家都种有小葱,也种有香菜,风调雨顺小民安乐真快活。
我们两家邻居性格和谐,兴趣和美。两家往来,竭诚相待亲如家人,我已过耳顺他们近八十,大家熟悉彼此兴趣和收成,享受人生至高的晴耕雨读;我做画多年吴叔叔夫人当年总是陪看,绝无巧言令色:“一辈子若只做一件事,即使只会这件事,也认真做好。”带有鼓舞与支持,后来叔叔鼓励阿姨也拿起毛笔,她便与我一起细数笔墨风流了。
有一天,我家门口杏花被冰雹打落一地,同时也得知隔壁邻居阿姨生病了。我后来无端想构图一匹马,它不是靠近的,不是真实的,我只想传达一种最直观的感觉,没来由一瞬间所感觉的“奔马”;思想人类的腿脚怎么这么短不如马长呢?思想人类天天穿衣打扮也没有裸马好看?那天画画只用墨汁,直到月亮挂枝头也没完稿。
后来听吴叔叔说阿姨正在医院熬着苦头,再没几个日头了。像我画的“古汉马”雕像无法奔跑的雄伟,也像大城小调的美丽与哀愁,得知后来阿姨归去天家,她再也无法搭我家便车了。
我们仍是吴叔叔家好邻居,叔叔长我家两人都近二十岁,算是两代人,听叔叔说他颜伯龙之女颜家宝老师教导的工笔,我们曾在后花园修剪心上的文艺灯芯,享受自己的世外桃源梦,当知“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太12:19-20)
杏花流水杳然去,阿姨走后我家杏花仍年年开,感谢主,近年吴叔叔的妹妹吴姑姑更常住乡下照顾哥哥,兄妹情深。总看叔叔与姑姑生活十足兴头,拿锄头种菜,随时乐观带头;阳光天天晒心头,尤其一早听到吴叔叔一句洪亮的问好,就像摇滚时髦的“安可”。生活,谁不快马加鞭认真奔跑?吴姑姑总给好吃的分享,谁会百无聊赖?世相本就复杂,这世界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总有离别有衰老。我总对他们的生活态度竖起大拇指头。唐时风,宋时雨,千百年来山还是山水还是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90:10)
那天听到吴家的叮嘱:“今天北京雾霾严重,在乡下挺幸福,你们别总是宅着呀!”狂逸率真的老北京人,他们大半生都在大城生活,几句话立刻让人想到王维的诗:“田夫荷锄立,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惠芳几次跟着姑姑出门去游山玩水了。
近日我仍画钟爱的“古汉马”,画它的凝固与承重,不怕风雨飘摇,颜色甚至涂抺中黄色,因为泛黄的东西看来岂不更温暖?“古”让人联想“旧”,旧一定是破、老、坏、臭?我看不然,即使在不相干的人眼里看来一文不值的玩意儿,在收藏家眼里可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花非花,马非马,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因为画而一无所有,因为画而无所不有。
老北京邻居文化很高,他们教我解读那落花就像化做春泥更护花,那是理想人生的总结,也是杰出的谢幕,直接意会圣经:“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怜恤。”(太5:7)
立冬后时我们又来山村踏月,刚买了一罐果农新酿的花蜜,蜜很浓价不高,皆大欢喜,就像我的生活小Honey。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北京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