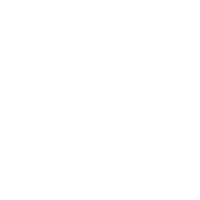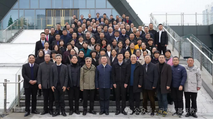我出生于台湾新竹,从小便知道新竹县是台湾人文最丰富的“县”,因为有两个国立大学:清华大学与交通大学,清大更高一席不只因为校园大、名声响,更因有名的创校人梅贻琦校长。我永远以这位基督徒老前辈为荣,当年我无缘考上清大因为它实在“高”,“清大”便永远是我的梦了。至今不忘小学毕业旅行进去了清华大学的梅园,即第一任校长梅贻琦的墓地,也永远记得从小学时代就有的“做清大学生”梦想。
清华校长梅贻琦离开60年了,也就是我出生那一年,他任北京清大校长17年,台湾清大校长7年,享年73岁。人人敬佩梅校长,据说当年他生病入住台北台大医院时,与大名鼎鼎的胡适同在一家医院,可惜胡适走了不多日,梅校长也永远离开了。贻琦当年是在留学期间信仰基督教,受洗成为基督徒的。其实梅贻琦的知名度很大,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不论在中国或台湾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大家早熟悉他的贡献与不凡。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最主要的成就是成功地维护并巩固了独立自主办学的传统,1938年西南联大的教授以及副教授共161人,其中清华的就占51%,有83人。当年梅贻琦的想法谁都支持:“学术自由,包容新旧左右,才能办出真大学,好大学。”难怪他是两岸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非常重要的一位,也难怪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许多基督徒更以他为荣。
知识界、教育界或文化界,梅贻琦都占一席之地,如今各界大师都想念他曾义正词严而又文辞雅说过的:“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以刻板文章,勒令从同。世界各著名大学之课程表,未有千篇一律者,即同一课程各大学所授之内容亦未有一成不变者。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
梅先生虽已离开六十年,如今岂不让我们更向他致敬?我住北京亦庄不止二十年,离北京天津都不过半小时车程,曾想过要去天津梅贻琦出生地看看,遥拜一下曾在基督教青年会打过工的梅贻琦。据记载,梅父坚持让长子梅贻琦在天津入馆塾读书,教育便成为梅贻琦人生的转折点,昭示着他曾说过的“生斯长斯,吾爱吾庐。”确定他当年崇拜司徒雷登 ,更确定司徒雷登父母都是传教士。
梅贻琦年轻时参加过不少基督教活动,可想而知为何常出现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活动。我们都知道基督教青年会(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简称YMCA)是相当社会化的组织,台北的YMCA就在希尔顿饭店后面,希尔顿是当年的第一家国际级五星酒店,而YMCA只是三星级的更是基督教国际性社会服务团体,即以基督“为世人服务”的精神。
据说梅贻琦特别随和,他认为“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难怪在1931年他提出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抗战困难时期物资匮乏,西南联大根本没有“大楼”,他就将“大师”作用发挥到极致,晋升登高,让生命学术齐增长并充分尊重教授,梅贻琦本着学术自由精神,尊重每位教授不强求一律,更不会厚此薄彼,阐述的精神岂不也是基督徒的, 让我们再想念主恩,感谢主恩。
在西南联大最艰难的时期,梅贻琦以及师生经过多次讨论最终确定“刚毅坚卓”为西南联大校训,尽力创设精神和学术自由的环境,查看许多梅先生的历史资料我想起一长篇小说《未央歌》,那岂不就是当年许多年轻的青男青女的梦?梅贻琦一生清白,一生清楚,还曾清寒到与妻子卖路边摊,特别多看了几遍他1940年曾在一次会上的发言:“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条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负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韧前进,虽然此时此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园。”
因为梅贻琦,直到今日我想念新竹,清大,梅园,因为永存暗香,有点乡愁。感谢主,在那不一样的时代给了我们不一样的梅贻琦。如今两岸杰出人才备出,不忘当年难堪的国难,难走的教育之路,更让我们多多念想梅贻琦。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北京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