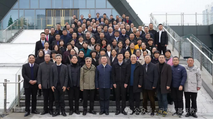我生长在农村,父母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在改革开放前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虽然父母勤俭节约,没日没夜地干,但是家境依然贫寒。我是家中的长女,底下还有几个弟弟妹妹。很感恩的是,即使在重男轻女的农村,在食不果腹的年代,父母依然送我读书直到中学毕业。学校时常有霸凌现象,我有时也遭到一些人的羞辱、排挤、孤立,于是很羡慕人家有哥哥姐姐。心想假如有哥哥姐姐,当我被人欺负的时候,就有人保护我,帮我“出头”。
我的生活很单纯,从家到学校,从学校到家,两点一线。我在家中不用干其它活,放下书包,就开始做手工活——编斗笠。可别轻看小小的斗笠,家中的油盐,身上的衣裤,孩子的学费,人情世故的开支,一切需要钱的地方,都靠卖了小小的斗笠换钱。而这些斗笠,是靠爸爸妈妈的工余时间——那时是集体合作制,他们都要去生产队干活,甚至被派到外地干活,没有工钱,只在生产队记公分,还有我的课余时间,全家齐心合力编起来的。一个斗笠从上山砍竹子、破竹篾、编竹篾一直到成型,有好多道工序,我只是做其中编竹篾的一道工序。从我八岁上学起,我的课余时间几乎都在编竹篾。
和物质生活的贫瘠一样,我的精神生活也是贫瘠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除了语文课本,几乎没有课外读物,偶尔大队部放映电影跑去看,都是放了又放的老片子。我的手飞快地编竹篾,思绪就插上翅膀,自由飞翔。我时常幻想有一个保护者,一个陪伴者,一个倾听者,他好像在我举头三尺的地方,好像在我的身旁,又好像在我的心里。他像我灵魂的父亲,以慈爱环绕我;他像我的兄长,陪伴保护我;他又像我的老师,以智慧谆谆教诲我。我时常幻想有这样的一位安慰者出现在我的生命中,但是他姗姗来迟,因而我内心时常感到孤寂、空虚,那种似有所缺、忧郁的感觉,时常侵扰我。
2004年,我已届不惑之年,写了一首诗《心灵之约》,以笔名“阿愁”发表在地方日报的副刊上。那是我心灵的真实写照。
心灵之约
今夜
我们一起去赴约 好吗
寻找那不经意间遗忘的
寻找那不慎丢失的
寻找那千呼万唤的
寻找那刻骨铭心的
或许高山流水会遇知音
或许无须倾诉便心有感应
从繁杂的事物中脱身
远离尘世的喧嚣与浮躁
今夜,让我们共饮一条泉水
邀请天上圆圆的月
做我们心灵呼应的见证
在茫茫人海中,我想约谁呢?去赴谁的约会呢?我自己并不知道,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冲击着我,促使我写下来。
多年后,当我加入教会,成为基督徒,在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爱中,享受到儿时渴望的那种心灵团契的美好,我内心的空洞终于被填满。我的人生终于有了方向,有了亮光,不再是出生入死,乃是出死入生。我不再否定自己的价值,否定人生的意义,乃是在上帝的爱中重新定义——我是天地之主的孩子,我是蒙爱的。即使在生命的至暗时期,我依然能得着安慰,并且靠着上帝所赐的力量走出黑暗。
有人说,上帝是外国人的神,是西方人的宗教渗透,是西方人的精神鸦片,是西方人要颠覆华夏文明的势力,一个中国人信了上帝,就少了一个中国人。
我说,宗教信仰是人类的共有情结。人与上帝的眼界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在人看来,有你和我、你家和我家、朋友和敌人、中国和外国之分别;但上帝只造一个地球,在上帝看来,全人类都是祂的孩子,都是祂所宝贵眷顾的。
拿破仑临死前说:“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师,现在却空无一人;我曾经横扫欧亚非三大洲,如今却无立足之地。耶稣远胜于我,他没有一兵一卒,未占领寸土之地,他的‘国’却建立在亿万人心中。世界上只有两种武器:信仰和利剑。在短期内,利剑可能凌驾于信仰之上。从长远的角度看,合乎天道的信仰必将打败利剑。”
有人问,上帝灵不灵?是否有求必应?
我说,上帝是全能的神,不是全能的奴仆;上帝是人敬拜的对象,不是人利用的对象。上帝有怜悯,有恩典,乐意施恩与人,听义人的祷告,祂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上帝不是木偶,不是傻子,任凭人摆布、调遣、使唤,需要时随叫随到,不需要时靠边站,弃之如扫帚。
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首诗《同赴上主的约会,好吗?》,发表在《福音时报》网站,以回应迷茫、苦苦寻找、挣扎的灵魂。我在诗歌中写到:“上主是虚空之人的满足,上主是孤寂之人的良友,上主是伤心之人的安慰,上主是绝望之人的拯救。”
基督信仰真的很单纯,不是劝人积德行善,不是劝人将功赎罪,不是劝人避祸就福,不是劝人去领一张天堂门票,乃是劝人回归生命之源,得享真神之爱。
我恳切地向你发出邀请,同赴上帝的约会,好吗?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福建省永安市基督教堂义务传道。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