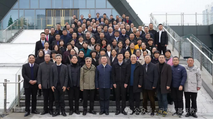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编者按】赵海翔弟兄,儿时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家人之间矛盾重重,无奈之下,年纪轻轻的他就外出打工谋生。在打工的过程中,他遭受了不少欺辱,最终沦落到流浪的地步,曾几次试图轻生。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几次得到爱心基督徒的帮助,给绝望中的他带来了盼望。此后,他走入了教会,成为了基督徒,还在主内建立了家庭,并成为了传道人。他的家族也跟着蒙恩,家人们陆续接受了基督信仰,家人间的关系也和睦了。以下是他的系列见证故事。
1982年的下半年,我随着大人到上海做泥水匠。初出茅庐世事无知,看世界万般无奈,看自己年幼无知。说是来学手艺的,天天都是无休止搬砖、 抬黄沙、扛水泥等等超体力的劳作。有时累得屙血,有时累得浑身难受。累的时候,我就想父亲:“如果父亲在我就不会如此了。”
泪眼朦胧,看那乌云翻滚的天空,好像漂落下父亲的眼泪。然后,看到的是老板山珍海味,我们青菜白菜米饭;老板翘着二郎腿喝着茶,抽着烟。我们累得腰疼背酸,口干舌燥,有时连喝水的机会都没有。你说这就是我对世界的看见,公平在哪里?仁爱在哪里?
还有一次,我在搬砖,同伙欺负我说我这么大人才搬三四块砖,其实我手上搬了七八块,当时我一气之下就将一摞子砖扔到那人头上,幸亏被当中的人推掉,不然那次就不堪设想了。那时,我血气方刚,大胆质问师傅:“师傅,我是来学手艺的,不是来做小工的。”后来师傅给我一把砖刀,那房主来将我砖刀夺走扔到水里。
到年底没有一分钱,因为是说学手艺的。结果回到家就是争吵,嫂子说我没有钱回来等等。看到母亲泪水流连,天天被欺负。我的心非常难受,觉得在家里就像在棺材里,闷着快要死了。
《圣经》上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传9:12)
1983年的开春,经过三四昼夜火车的嘶吼,我来到了新疆。从此整天搬运石头,我实在体力不支,鼻孔还总是流血。领我的陈师傅还是强逼我干活,并用钢筋抽打我。有一天,我正干着活猛然眼前发黑晕倒在地下,陈师傅将我提回宿舍扔到床板上。第二天,丢给我两块钱让我去连队医院诊治。于是我就捏着两块钱出了门,走到半路就又晕倒了,幸亏部队战士将我送到医院。陈师傅去领我回来时,一路上骂骂咧咧,还没到宿舍,他就又回到工地了。我摇摇晃晃往回走,一阵心酸又晕倒在路边。我被一位好心的阿姨搀回家。在这片异乡的土地,受到这份关怀和爱,使我泪流满面,无限感动的咽下了她给我做的一碗鸡蛋面条。
中秋节快到了,队里发了月饼,但我吃不下。我望着天空,想念远在家乡的母亲。她那流泪愁苦的脸从没有喜乐过,她能吃上月饼吗?我心里实在不愿独自享受,就将月饼给了陈师傅说:“师傅,这个月饼就算给我母亲的孝礼,送给你代吃吧!”结果他随手将月饼扔给了一个常欺负我的丁师傅,那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大地伤害了我的感情。我心里何等伤痛,再好的心对陈师傅,他也不能像上帝一样爱我。
一天天的过去了,我根本没有学到技术,人却越来越消瘦。我就写信给大姐,要她给陈师傅拍电报让我回去。就这样我拿到一张火车票和三十块钱,走上了回家的路。到了家,就像进入棺材一样,表姐的脸每天都拉得很长。母亲还是跪在“菩萨”面前求平安。我小时候就有的腹痛也时常加剧。父亲的一个巫师朋友常让我吃香灰、喝仙水、去拜庙、祭祀来医治腹痛。病情却依然如故,越来越严重,就是医院也没有查出病症。
可怜的人类,什么是黑暗的权势?这就是:在外被人欺,在家被鬼压。母亲心疼我,为我流泪、为我求。表姐却因此对我又吵又闹,让我干活不肯罢休,这时我真不知道这个“菩萨”身为何物,为何不能带给我们全家一丝的平安呢?
1984年初,舅舅托人给我找了一个活,到江阴南闸采矿厂去拉石头。每天的任务是六十五车,每车负重八百多斤。我忍受着生活巨大的悲痛,总以为能够挣到钱就是出路,所以,哪怕鼻孔天天出血,也坚持上班。同事说,你年龄太小,做伤了一辈子残废。尽管有时候爬上楼梯就晕倒了,还是第二天坚持上班。超强的体力,终于有一天鼻孔出血不止,工段长将我抱起来去医务室止血。止了血浑身疼痛难忍,就领了些免费的膏药前胸后背都贴满了,同事说“这可省的买衣服的钱了。”我还是不休息,别人放假我不放,别人休息我不休,就这样强忍着干了一年,挣了两千块钱。但是对于这穷困的家庭,这点钱根本不能做什么。
1985年,二姐看我体弱多病、力量小,就劝我学裁缝。裁缝师傅邢振发对我很好,也很关心我。我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技术,第二年家庭的战火继续升级,我不得不终止学艺,就办了出师酒,答谢了师傅,告别了学艺生涯。
1986年,经人本队兰芳姑姑牵线到常州电视大学服装厂上班。老板每个人发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就卷起所有的钱逃跑了。我怀揣着八十块钱,想在城里买点好吃的带回去给我母亲,结果,被一伙人劫持到一条河边,软硬兼施,说他们偷来的茶叶要叫我买下。我说没有钱,他们几个人就将我抬起了要扔到河里去,这时他们中的一个人打开我的包,抢走了我的钱,扔下一皮包茶叶,里面还有带公章的介绍信。
我回到家经人鉴定都是假的,我心里就如万箭穿心,因为,我没有钱到家就会使家庭不得安宁。悔恨自己为什么不能战胜那些人。于是,我带了仅有的十块钱,悄无声息离开了家。我决定寻找到那帮劫匪,讨回我的八十多块钱。
我步行到南通,花了一块七毛钱坐船到上海,又从上海坐了八块钱火车到杭州,口袋里的三毛钱一直保留着。我按着地点找到杭州茶厂,说明来源,茶厂的人非常热心,帮我鉴定茶叶,而且鉴别介绍信,说:“我们杭州只有茶厂,没有西湖茶厂。”他们问我骗了多少钱,我说:“八十块钱。”他们笑得合不拢嘴,“这八十块钱你来找,人家被骗上万的多的是。回去吧,找不到了。”我不死心,我找遍杭州城的大街小巷,按照劫匪说的地点,都是国营单位(当时社会没有私营的)。我才如梦初醒,才知道自己涉世不深,上当受骗,天真幼稚来找骗子。当时是想找到骗子要了路费回家的。现在回家的指望没有了,三毛钱早就买了水喝了。
面对人间天堂的杭州,我却是她的垃圾。我望着西湖水,碧波荡漾,清澈见底,猛然感觉到死在里面多好。游玩的人络绎不绝,我和这个城市形成了明显的反差。那些人酒足饭饱,而我饥肠咕噜,也想为肚子找点安慰,看到别人扔下的西瓜皮狼吞虎咽地吃个精光。饭馆里的香味常常使我留恋,不愿往前走,等待我的常常是服务员的扫帚把,大多数乞丐干脆在垃圾桶里找食物。
要想回家,没有路费,只好沿铁路步行往上海方向长途跋涉,于是日夜赶路。夏日的夜蚊子格外欺生,累了想休息,就被蚊子赶走。几天下来,衣服异臭难闻,就是裤头汗衫。白天就跳进河里让衣服冲一冲,将衣服晾干,再继续赶路。有一次深夜大雨滂沱,我奔走在杳无人烟的漫长的铁道上。突然“噼啪”一声,震耳欲聋的雷电将我旁边的树劈成两半,吓得我魂不附体。
几天几夜的赶路,又累又饿,多少次昏睡在铁道旁。偶尔遇见人家的菜地,就一头扎进去,哪管有多少尘土覆盖的菜叶,就揪下来大口大口地咀嚼起来。亦或在看到一片片青草地,就像饿羊一样贪食的吃起来,也没有感到什么难吃,总是那样的津津有味。有时,从村子里飘来美味佳肴的香气,让我忘记了棍棒、狼狗、和羞辱……
好不容易半个月的徒步,终于到达了上海。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