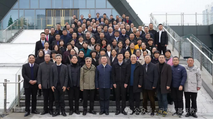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是纽约救赎主长老会提姆•凯勒牧师(Rev. Tim Keller)对纽约各派别基督教会历史的思考。他在文中提到新教教会中不同派别如长老会、浸信会等的社会参与,以及教会对社会世俗化的回应方式。他提醒教会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最近,我读马太•鲍曼(Matthew Bowman)的《城市讲坛:纽约和自由福音派的命运》(牛津,2014年)。这本书讲述了纽约最初建立的教会是荷兰改革宗教会和圣公会教会。接着18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的由乔治•怀特菲尔德等人带领的大觉醒运动,则强调通过听到福音宣讲而悔改的重要性。
尽管传统的教会拒绝怀特菲尔德和需要悔改的福音派理念,但新的长老会接纳了他。在18世纪的进程中,第一浸信会的牧师约翰•加诺(John Gano)和第一长老会的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所领导的这两个宗派包含着福音事工,其成长和蓬勃发展超过了其他宗派。第一长老会建立在柏树街(后来的第五大道),罗格斯长老会也在那儿。第一浸信会也见证了许多新的浸信会开始在城市及周边建立。到19世纪的上半年,福音派基督教在纽约已经是“文化共识”,并已经达到“文化优势”。在1857-1859年的富尔顿街大复兴可能是其高潮。
然而在此之后,新教教会开始面临穷人和天主教居民人口的快速上升,尤其是在曼哈顿下城。在那里,新教教会发现自己的会众人数在急速萎缩。他们的牧师猜测非基督徒将会是文化新教徒,这些文化新教徒将认为他们的教会是一个应该去的地方,而且他们应该会理解讲道。但现在他们被一些弄暗新教之门的人包围,而且发现他这些人说的很多都难以理解。
鲍曼还注意到,到19世纪80年代,纽约市成为了第一个商业化的首都城市,充满了餐馆、商店和剧院,简单地散步、逛街、吃饭成为过去。这破坏了前去参加教会的吸引力,而去教会的吸引力一直是依赖公共饮食、音乐、聚会、以及社会指导,吸引邻居前来听宣讲的上帝话语的主要形式。现在,所有这些支持性的社会结构已经被取代。
新教教会是如何回应的?起初,他们只是简单的从更多的多种族的、商业化的区域,搬到新教地区城市中央公园附近的地方。另一种策略是竖立巨大的、宏伟的、美丽的建筑和圣殿,试图吸引人进入,并且以此方式声称他们存在于公共空间里,从感到被驱逐的地方来到这里。但这一切都没有停止新教的衰落。
最后鲍曼描绘出危机是怎样分裂教会的。慢慢的,但肯定有人开始远离宣讲中的信心、传播的教导以及真理带来的悔改。更加具有学术水平的像协和神学院的查尔斯•A•布里格斯这样的人物,教导说《圣经》中包含错误、《圣经》中只有主要的故事脉络是神的话语,引导我们的还有人的理性和经验,而不是唯一的《圣经》。为了吸引现代的人,有人认为,我们不得不放弃一些信念,比如《圣经》是完全真实的而且是改变所有生命的关键。
在实践层面上,长老会牧师像在布里克长老会的亨利•凡•戴克试图通过艺术和审美体验改变人们,而亨利•斯隆•科芬在麦迪逊大街长老教会首创了提供社会和教育服务的全方位服务的教会。鲍曼写道:“自从宗教改革以来,如果救赎的来到,在过去是随着聆听历世历代的传道人宣讲信息,在纽约市……救赎现在通过行为来到”比起试图通过转变人的的信念来改变人,教会应该寻求通过爱心行动、社会改革和教育,来让人们跟随基督。
其他回应城市世俗化的行动的是由浸信会领导的。当长老会和其他宗派走向了所谓的自由主义时,浸信会走向了后来被称为的基要主义。 牧养了第一浸信会将近50年的I.M.霍尔德曼,和各各他浸信会的约翰•罗奇•斯特拉顿,向城市发出一个非常好战的姿态。基要主义者的宣讲也远离了历史性的宣讲,因为它开始更加注重物质和道德上的罪恶,如酗酒和淫乱。为了显示这两条路径越来越多的分歧,鲍曼有两个总结性的章节,一个是基要主义者斯特拉顿,一个是河滨教堂的第一任牧师,自由主义者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
一篇很短的通讯文章当然不可能避免以偏概全的通病。然而,这很难不让人发现在20世纪下半叶,传统的新教福音派——真实的历史正统教义,但也理智稳健和社会参与——在纽约市已经非常微弱甚至消失。但现在它又重新增长了。至少有100个的教会,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过去的20年已经在中心城市纽约(和一些复兴的老教会)开始,它们更接近那种曾经在这里蓬勃发展的旧式的基督教。然而,我们也面临着一个文化的问题,就是对我们不得不说的事物不感兴趣。我们如何达到?
我们绝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绝不能以离开作为回应,也不能以符合同化的时代精神作为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