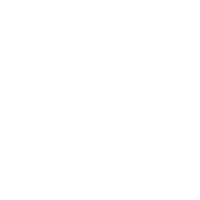19世纪的时候,整个基督教遇到了挑战,即如何应对现代思想。在这个问题上,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不太一样。
天主教会对于那些所谓的比较现代的哲学和神学思想,特别是一些文明的新成果,比如进化论,采取的方式是用教律来反对,就是说天主教徒不应该去读这些书。每年,教会都会出一个单子,列出天主教徒不应该读的“禁书”。
基督教则相对开放一些。
但到了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则是天主教的神学思想更开放一些,基督教的比较保守。
19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之所以有一种演进,是因为交通技术的跟进,比如蒸汽机、船舶的速度比以往更快,这就使各个大洋之间的人口流动比以前快。原本稳定的家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解构”,大家族开始分化。因此,人获取经验的渠道也和以前不一样,“我”开始作为判断事物的一个基本单位,19世纪就开启了一个“崇尚自我”的时代。
有些神哲学家认为,“崇尚自我”的时代开始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因为这位改教家一直要追求的就是如何可以晓得自己是被上帝过拯救,所以,这种对于“自我”的珍视,其实也是宗教改革的一个产品。
相对于以前来讲,就是在19世纪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人们会认为“过去的是最好的。”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观念,比如“你要拾起,你要重新找回起初的爱心”,认为以前的都是好的,现在的不堪和软弱都是因为我们放弃了原来好的情况。所以,不少传道人会呼吁回到原来。
但从19世纪开始,许多的发现,如地理和生物物种,让人们觉得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他写的《物种起源》。他的看法是,历史在演进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是没有办法回到过去的,因为“人在发展,世界在发展,历史也在发展。”人们应该能够向前看。而这个“往前走”,对于基督教会有许多的挑战。
比如,基督教所谈论的东西,能不能回答人一切的问题?从19世纪开始,这个问题就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就是说,好像基督教不能解决科学和自然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有人问,我们研究基督教有什么用处?我知道上帝多一点,能够给我带来什么?
在中世纪,基督教能给人一个世界观和人生的理想,因为那个时期是神学贯穿的时代。但是19世纪,随着科技和文明的发展,人们就会问:我研究上帝多一点,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卡尔·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观点就对于基督教来说,“挑战”多于“帮助”。这两个人都是“世界在前进”理念中的助推者。
他们告诉我们,看待世界和自己,不能再用以前的老眼光来看, 否则的话,就会撞墙。那么,用什么来看?可以得着什么?
冈萨雷斯就提到了一些人,一个是施莱尔马赫,德国有名的神学家,从他开始,人们对于《创世记》的解读有了新的方式,即这章经文不是要解释世界是如何成为现在的这个状态,这是科学要来解决的,它告诉我们的是世界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这是寻求永恒上帝的过程。对于他来说,基督教是一种人们对于上帝的炽热的情感,“我仍旧可以是基督徒,我仍旧可以是基督徒,在这样一个信仰受到许多的一些摧残的时代,但我仍旧可以是一个基督徒,因为我仍旧需要,仍旧需要信仰。因为信仰是使我的生命可以建立,这样的一种的因素。”
另一个是黑格尔,他的学说跟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中国,他认为,中国其实是没有历史的,有的是一个王朝兴衰的循环。就是说,西方的历史是线形的,但中国的历史是一个圈形的,出发然后又回到原点。
他观察历史的看法来自于基督教发展的看法。他觉得,历史如同戏剧,有正面的力量,也会有负面的力量来搅扰它。正负力量之间的争战之后,正面的力量更加强大,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境界,形成新的高度和制高点。又会有一种负面的东西,希望对它有所牵制。世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匍匐地向前进。他用这样的规律,不仅来研究历史,也研究整个人类的生存状况。
还有一个人是克尔凯郭尔。康德注重“道德”,施莱尔马赫注重“感觉”和“体验”,克尔凯郭尔注重“信仰”,他觉得,信仰不是消遣,而是一种性命攸关的东西。对于中世纪来说,宗教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一个国家的政治观,是维系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到了克尔凯郭尔时代,他认为,宗教是和人性命攸关的,涉及人的终极观,我们的信仰必须建立在生存的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