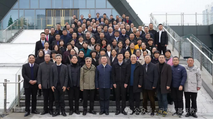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林后6:10)
感谢主!助我得获云南保山余文开牧师的协助,还有当年富能仁曾两次会晤的朋友后人贝丝(Beth Leach)多次从加拿大来邮:“我父母在中国宣教时,曾两次聆听富能仁的钢琴演奏会,1927年那次在烟台,富能仁完全以记忆弹出贝多芬钢琴曲系列;1930年那次在上海,遇到富能仁带着心爱的新娘来共餐,他再为我们弹琴……”加上四川以诺公司协助几张照片,再加以富能仁女儿艾琳(Eileen Crossman)著作《山雨-富能仁传》(Mountain Rain)一书,笔者得以完稿。

下笔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自英国泰晤士河畔远到中国怒江大峡谷宣教(1908-1938)前,笔者对少数民族傈僳人几乎一无所知,相关书籍或报导也极少提他1908年抵中国的时代大背景,其实那是人心惶惶宣教最难时,一败再败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及庚子之乱,清朝帝国余息尚存但仇外反教最烈,秋天时慈禧与光绪相继去世社会更动荡不安……
而内地会创始人戴德生曾在19世纪末返英,大家才知有个不认识耶和华的广大土地叫“中国”,每个月都有近百万人在不认识耶稣的情况下死去,距今,内地会创满150周年,富能仁正是当年被激励的麦子之一。
当时,英国富家子弟富能仁一直关心内地会及戴德生,1906年20岁的他自伦敦大学毕业的个人钢琴演奏会后,前途一片大好。
富能仁却在读完一本小册子《Do Not Say》后发现:“人应放弃自己的计划,因为神有更好的安排。”因此他一直想活出基督式的生活。接着两度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均因有耳疾被拒绝,第三次终被通过了。
1908年,22岁的富能仁已到上海开始学习中文。初抵中国他便识剑桥七杰之一何斯德(Dixon Edward Hoste),当时戴德生刚过世两年,不论中国或中国的基督教都疲累无依,年轻的富能仁所有做法即使有腔调也很低调。
次年,富能仁终于抵达云南,他骑着骡子抵达腾越(今腾冲)走入傈僳族。骡行速度慢,这位年轻人骑在骡上,常读乐谱用以亲近古典音乐,因为那是没有收音机录音机的时代。
余牧师告诉我:“富能仁刚到西南山区,是骑骡走村串寨对汉族传福音,但成绩不佳归依信主寥寥无几,汉人甚至待他并不友善,一度让他沮丧,富能仁却在傈僳族里体会到少数民族的单纯与需要。一直热爱音乐与户外运动的富能仁决定留下来传播福音,他开始开荒布道。”也没想到这一待是富能仁的一生,他为中国西南写下重要的使徒行传。
那天,傈僳人余文开牧师刚自缅甸返云南保山接受我电话采访,由他介绍富能仁当年点点滴滴更具说服性:“傈僳人历代沉浸在拜鬼的风俗里,没人听说过耶稣基督。”

余牧师的爷爷曾说富能仁初到腾越的那些日子,年轻人最大的挑战就是孤独;在高山深谷里宣教,要与神同行,自我节制再次变得极其重要,宣教常令他沮丧,他常随身带本赞美诗到山顶望着整个腾越,为这个地方大声祷告。他已懂得不让冷漠、自私腐蚀自己的心灵,尤其对带有耳疾的年轻人。
余牧师:“文化不高的傈僳族没有历史,因为没有文字,只信鬼魅没有信仰,直到富能仁为我们创造傈僳文,还为我们翻译新约《圣经》,傈傈族才开始听到福音。”
余牧师再补:“富能仁常常用音乐靠拢傈僳人,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也有令人沮丧的时候,有的信徒好不容易归主后,又回头去拜鬼,还有次是个弟兄染病死了,那事曾大大动摇信徒的信心。”富能仁即使曾在传福音时无助过,像是神的恩典在托住他,难怪富能仁说:“没有神的动工,我就像是一个人把船搁置在浅滩,不论是拉还是推,最多只能将船挪开几英寸,但若等到涨潮再将船冲到海里轻而易举,毫无阻拦。”年轻人拥有这样的见地,简直就是上帝特派的。
也有同工:“富能仁每次尘土满身回到腾冲时,就直奔风琴,把自己沉醉在音乐里。他不用看谱,弹奏巴哈、贝多芬、舒曼和肖邦等人的乐曲,常常一弹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时,你不能去催他喝茶吃饭,因为他对音乐的饥渴必须先得到满足。”他曾多次以音乐感动少数民族,以旋律拢获傈僳人。
云南夏季(6-8月)的雨占一年的六成,可想而知阵雨季节宣教更苦,于是在雨季圣经学校的人也愈来愈多,还培育了许多传道人。曾经一场宣教后,他拉动手风琴还唱起歌来,愈来愈多傈傈人靠拢……一位年轻人走出来并笃定地告诉富能仁:“我要跟随耶稣!”那位跟随者叫莫丁昌,一个做面师傅;但富能仁觉得他已略懂耶稣,也知道“马可福音”,原来是富能仁常到市集或菜场发福音传单时,曾有人偷走他的单张福音纸,也有次大风吹走许多宣传纸,曾有孩子捡走拿回家了,那人就叫莫丁昌,福音果子开始一个个结了……那年夏天,他说:“神啊,让我看到傈僳人归主,我就真可以这么说:‘我在猪栏里也快乐!’。”
也可以说,富能仁结束英国的富贵无法继续弹琴,虽远在边陲仍独奏自己生命的乐章,从没间断!岂不正像休止符号,因为曲子奏到休止符时会停歇,但也让人屏息……

余牧师:“我们历代傈僳人都有拜鬼风俗,没人听说过耶稣基督,但是富能仁已给傈僳族信心,只是成绩一直不佳。”当又有12个人发誓要做基督徒,富能仁也发现几乎没有人愿意按时聚会。“我不能操之过急,但我祈求神的恩典,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神到傈傈人中工作的收获。”富能仁又经过六年时间已有深刻心得,思考着是否应该转移其他地方宣教。他又探访了几个小镇,用汉语给当地人讲道。
有天早上富能仁已打算离开,傈僳导游突然告诉他,有个家庭想成为基督徒,让富能仁给予帮助。他给这个家庭的人讲了如何信耶稣,接下来,超过七个家庭拆了家中的偶像,不再拜鬼纷纷归向基督。
“山雨”中富能仁写回英国的第一封信:“我深刻体会到,不管手边工作多么微不足道,只要是神交托的就要尽心尽力去做;生活中,我常常遇到一个以各种不同方式反复出现的试探……”

富能仁还写信给妈妈:“傈僳人听道时总站着听,因为桌子与椅子对他们都是奢侈品,家里除了一个灶没有高出地面的东西,我曾睡在只高出地正两三英寸的地方,女人戴着许多珠炼首饰,如果换妳挂那么多东西脖子一定受不了……他们正在同我学习傈僳文学习如何使用要理问答,男孩女孩对我拿笔写字这件事很感兴趣,我告诉他们快去看我送的书……”
余牧师说目前云南傈僳族大约六十几万,加上中南半岛、东南亚及海外的顶多一百二十几万。他家一门五代信奉基督绝无二心,就是富能仁当年在他爷爷那辈开了场白,如今富能仁已被公认是基督教东亚最成功的宣教士之一。
余牧师从小对富能仁耳熟能详,直到他96岁痴呆症爷爷临死仍牵挂富能仁在中国边陲的安危,还有对汉族的排斥甚至仇恨心理:“我们傈僳族打不过汉人但让得过,汉人无法让我们信靠,几世代傈僳人被挤被赶到蛮荒山脉,我们没本事就始终靠什么随什么,后来大量傈僳人笃定地信奉基督,就是因为富能仁……”难怪富能仁也说:“每一件神的工作,皆如那燎原的星星之火。”
好几次电话采访那头余牧师情绪激动,性情真实,听得出那是傈僳人感念傈僳使者富能仁:“我们傈僳人贫困且多文盲,天性贪生怕死又不团结,信奉鬼魅但没文字也没文化,我们从何而来,我们如何而去?祖先没留下足够的知识;汉人说好听是聪明,实际是诡诈、狡滑,我们一直与汉族不兼容,信仰、语言、习俗更不同,但是富能仁带着真爱加入傈僳族,他带我们爱主,而且时间累积愈久我们愈爱他,我都有孙子了,家里现在是第五代基督徒。”
余牧师谈的岂不正是马太福音5章1至3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几百年来傈僳族住在怒江大峡谷,大山大林里野兽出入土匪横行,富能仁出现给傈僳族依靠并信任,他是我们的傈僳使者!”富能仁渐渐牧养着至少两百户基督徒家庭,他也明白是该编写傈僳文字并翻译福音为傈傈人出真理小册子的时候了。译好的书尚未印出前,教傈僳人认字着实费力,富能仁留的笔记得知,总几个人围着手稿坐着,结果有人看手稿是倒着,有人侧着的,轮到下次坐的位置不同又认不了手稿了。
富能仁1922年返英过圣誔节是他首次度假,当年曾告诉英国同工:

“我给中国人传神的福音,和你们把衣物包好,交到裁缝手里之类的事情,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同样做主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不是由我们自己去选择的,假如神已经替我们选择好了,我们就放胆去做,还用得着再等待那些更大、更好、更神圣的工作?”
富能仁休假两年中还去了一趟加拿大,此行又是一重要之旅,因为杨宓贵灵(Isobel Kuhn)与她未来的丈夫杨志英(John Kuhn)也因富能仁后来赴云南傈僳族传福音,杨宓贵灵后被称为“傈僳人的使女”,这岂不都是神的旨意?
再返中国,富能仁先被派甘肃,1928年再被委任内地会云南总监重返云南,得以重返他热爱的傈僳族中。内地好友何斯德已渐渐觉得:该给已过四十岁的富能仁介绍个好妹妹了。但富能仁不修边幅的外型常让许多人低低发笑,他也不以为意:“在陌生的地方我看起来像什么不要紧,反正没有人认识我;在一个熟悉的地方,我看起来像什么也不要紧,反正每个人都已认得我。”
1929年秋天,43岁的富能仁在昆明结识23岁的妻子洛西(Roxie Dymond)并结婚,婚后有近半年时间里,夫妇两人长途旅行遍访各传教区。1938年九月,雨季稍歇,富能仁却在云南保山得了脑虐疾去世,年仅52岁,还留下三名年幼孩子。

毫无疑问,他的人生太短,但宣教却是丰富且成功的,据知1950年时,已有七万傈僳族跟随耶稣,1995年已逾十万基督徒,目前傈僳族有九成是基督徒,传教使用的圣经及赞美诗仍用富能仁当年创造的老傈僳文写的。
辅以《山雨》书开头:“一个克钦族猎人手持砍刀追杀富能仁,但在这本书的结尾,当富能仁去世后,这个克钦猎人来看富能仁的妻子,告诉他因着神的爱,他已经成为一名基督徒。”
“富能仁早先的墓地被划为军事用地必需迁走,不得已,傈僳人合力移走尸骨重放一罐,拿到青华教会庭院中重建另五公尺高墓碑,那墓碑就是我2002年设计的。”余文开牧师在电话那头说,傈僳族对富能仁的感恩从碑上两首对联可见。
上联:“依靠十字架,不再从虚假。”
下联:纵使辛劳直到死,为主劳苦神赐福。”
墓碑上还有用英文、中文及傈僳文写的约翰福音12章24节:“一粒麦子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粒来。”当年富能仁传教播种时肯定流过泪流过汗,如今却欢呼收割,正像结粒的麦子。

可以感觉余牧师语气里的温暖与体贴,尽是无限感恩,正是民数记六章24至26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 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
完稿前我始终静思:是什么样的爱,让一个22岁年轻人愿意远道而来,放下尊贵选择穷山峻岭宣教,有耳疾的人不宜住高山,但富能仁最后还把生命终结在此?
怒江大峡谷高度多半不止五千公尺,即使深谷也在两千公尺以上,想想当年总有圣歌弥漫,雨季时富能仁总在滂沱中仍卖力传教,富能仁的生命高度——难怪让我们后人想永远对他仰望。
感谢主,让我们有此好弟兄,我们以富能仁为傲,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