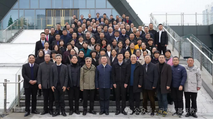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现代性”的本质既然是“人本主义”,就不是靠任何人类文化的优良传统可以改进的,而基督教的超越性也是任何文化所无法比拟的。[1]因为基督教所信仰的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一位具有无限位格的上帝。只有他才能与人建立起真正的神人关系,人们也只有透过基督教信仰才能真正拥有向无限他者开放的可能,这样的追求才是能真正转化生命、克服“人本主义”的一剂良药。[2]当然,中西文化作为人类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仍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尤其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天人合一的理想,圜道观的思想都是非常独特的。由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大自然视为一有德性的他者,其理想就是要仿效这无限他者,并努力与其合而为一。问题是“大自然”只是受造物,充其量也只是有限的他者,因此,这样的理想是很难实现的。齐宏伟就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症结在于其理想过于完美,太过高远,是人无法企及的。为了实现这理想,中国的古人走了两条相互对立却又殊途同归的路,就是道家的“自然主义”与儒家的“入世主义”,[3]前者强调“融入自然”,后者则是“将自然纳入人性”。
结果,前者失去了人的独特性,[4]而后者却走向了世俗化,将“人道”完全等同为“天道”,以致逐渐僵化,丧失了道德生活的动力。[5]虽然如此,道儒还是有着积极的一面,如,道家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及儒家的“中庸之道”,这些思想如果结合基督教信仰就能大放光彩。因为基督教的核心信念就是“十字架的道理”[6],是以柔克刚、以善胜恶、以死入生的“二律背反(Antinomy)”[7]的真理,这样的真理使得“圜道思想”具有了真正的本体,强化了它的应用。针对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两极分化、弱肉强食,若要营造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则不单靠健全的法律制度,更当多多注重“十字架的道理”及“物极必反”的“悖论”。还有,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精髓,而基督教伦理学正是一门注重动机与实践的学科,二者结合,并以基督教信仰修正儒学的不足之处,既丰富了基督教信仰,亦成全了中庸之道。
此外,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对话也能减缓此二者的排他性倾向。首先是减缓基督教的排他性倾向。毋庸置疑的一件事就是,基督教的确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因为基督徒信仰的是独一的真神,而基督教的真理原则也是不容妥协的。不过,这并非基督教的全部。除了排他性,基督教也同样强调“包容性”,保罗教导罗马教会的信徒,“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12:18),教导以弗所信徒“凡事谦卑、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弗4:2-3)。彼得也教导信徒“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彼后1:7)。主耶稣更是教导他的门徒“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太5:44)
其实,基督教带给人们排他性感受的真正原因,不是她的“独一神信仰”,[8]而是没有处理好“排他性与包容性”之间的关系,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来说,就是没有实行中庸之道,将绝对的真理相对化,却将相对的观点绝对化,该坚持的没有坚持,该变易的倒是紧抓不放,且时常以非黑即白的简单逻辑进行批判,导致给人一种极其狭隘、极不宽容的感受。其次是减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排他性倾向。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文化的确具有海纳百川的肚量,但至少它对基督教仍有某种程度的“不接纳”,而这一种的“不接纳”也是与对基督教的不了解有关。[9]也许,我们的同胞仍以为基督教就是西方来的宗教,是反对祭祖、不接纳中国文化的宗教。民间有种说法——“基督教与民间宗教是相互对立的”。尽管如此,我们的同胞却不了解基督教信仰的精髓,是一种“二律背反”,同情弱者,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德性信仰。尽管基督新教在不恰当的时节入华传教,但平心而论,传教士们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是完全没有贡献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是抱着宗教的热忱来华传教,并且更是深深热爱这片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华夏大地。[10]
从理论上看,基督教信仰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在致力于促进整体的生态文明及和谐社会的构建。如果单从基督教一端来看,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要进行两方面的建设,一是,促进教会内部的灵命培育与教制建设;二是,拓展基督教的社会性事工。笔者认为中国的基督教应当多多关注当前社会的需要,努力融入中国社会,推动社会公平正义,构建一种中国基督教的公共神学。[11]
————————————————————————————————————
[1]刘小枫认为“基督事件对人类的民族性思想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闻所未闻和不可思议的信息”,见刘小枫,《圣灵降临的叙事》(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页98-99。
[2]温伟耀将人向无限他者开放的情形称为“基督教‘对话式’的自我超越”,伴随着此种相遇而来的是对那人世界观的“解构”与“重构”,这与中国文化中儒释道之“境界性自我超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见温伟耀,<论基督教与中国信仰中的超越体验>,载于卢龙光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2001),页212-216。
[3]齐宏伟将前者称为“人天合一”,称后者为“天人合一”,见齐宏伟,《启示与更新》,页218。
[4]如庄子在“齐物论”篇中的论述,首先庄子强调人们不应当从“是非观”的角度去看待事物,在庄子看来“是非”永远是相对的。其次,庄子甚至认为“认知”的最高境界就是“物化”——“物我及人我达到无差别的境界”,见孙通海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32-33、51-52。
[5]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载于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页273。
[6]斯托得认为新约最主要的作者都相信基督十字架的中心性,见斯托得(John R. W. Stott)著、刘良淑译,《当代基督十架》(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2),页33。
[7]是指在两个似乎都是合理或必然的结论之间的外表上的矛盾,见赵中辉编著,增修订版,《英汉神学名词辞典》(台北:基督教改革宗翻译社,1998),页26。
[8]当然也有教外的同胞看基督教的独一神信仰及坚持圣经的无谬误为基督教的霸权主义及西方的原教旨主义,牟钟鉴,<基督教与中国宗教文化生态问题的思考>,载于张志刚、唐晓峰主编,《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第一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页86。
[9]赵紫宸认为基督教的国际问题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教外的中国同胞对基督教的误解,见赵紫宸,<中华基督教的国际问题>,载于燕京研究院编,《赵紫宸文集第三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页163-164。徐以骅认为在上个世纪初至五十年代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在华的基督教会至少有三次与中国社会进步事业相结合的经历,已足以摘除其“洋教”的称号,见徐以骅,<如何理解中国今日之基督教>,载于邱如意责编,《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论文集——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上海:中国基督教两会,2015),页104-105。
[10]就如沈迦的力作《寻找·苏慧廉》以精确的考据及翔实的资料展现了一位虔敬侍主,也是热爱中国文化及中国人民的传教士,见沈迦,《寻找·苏慧廉》(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页31。
[11]“基督教公共神学”乃指将基督教神学延伸至社会公共领域,主张基督教伦理的基本观念不仅是基督教信仰的道德律令,也应该对公共生活(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道德和灵性结构有所承担,见谢志斌,《公共神学与全球化:斯塔克豪思的基督教伦理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