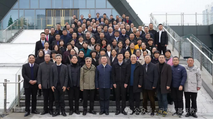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编者按】赵海翔弟兄,儿时家境贫寒,父亲早逝,家人之间矛盾重重,无奈之下,年纪轻轻的他就外出打工谋生。在打工的过程中,他遭受了不少欺辱,最终沦落到流浪的地步,曾几次试图轻生。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几次得到爱心基督徒的帮助,给绝望中的他带来了盼望。此后,他走入了教会,成为了基督徒,还在主内建立了家庭,并成为了传道人。他的家族也跟着蒙恩,家人们陆续接受了基督信仰,家人间的关系也和睦了。以下是他的系列见证故事。
一种莫名的力量催促着我的自行车向西直奔。我的大脑一片混沌,因为我没有方向更没有目标。只是想起了悲惨的生活和痛苦的家,激起我往前走誓不回头的想法,直到我疲倦时才停下来。不知不觉中已走了一百多里路,这时,才恍然问自己往哪里去呢?
顿时,想起了和母亲分别的那一幕。母亲挽拉着我的手:“儿啊!往哪里去?娘心疼啊!”看着母亲那张日渐憔悴的脸和单薄的身躯,我是多么不舍得,多么不想走啊!然而我强装着笑脸哄娘说:“我去香港,找条出路,娘,你在家多吃饭少开口,常常去姐姐家散散心。你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其实我的内心是多么的难受啊!也许,这是和娘最后的诀别了。想起娘最后松开我双手时,那脸上忧伤无奈的表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那天母亲说肚子有点不舒服,要去红医站。我就丢下她,她独自孤零零去诊所了。于是我不顾一切地骑着自行车离开家门。我心深知,此次一别,母子何日能相逢,在我里面是不可能的。
那股黑暗的力量,始终催逼着我。使我想死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于是,我被死亡的脚步催动,开始了闯荡“鬼门”的行动。
我骑车急行路中心,使路上的卡车一声急刹车,吓得司机舌头伸出半尺。探出头吼我一声:“找死啊!”我坦然地说:“知道何必停车呢?”司机看看我忧郁的面容没再理我,开着车走了。我又再次紧闭双眼向人群中撞去,公路上发出一阵惊呼。终于我被一辆自行车刮倒,前轮套住一女子自行车的后轴心,将我拖出去十几米远,等她下车后,看到我满身多处肉破血流的惨状。没再说什么,骑着自行车走了。一路上,我总就寻隙能让人打死或杀死,但总似乎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保护我。
开始几天还有力气,但渐渐地我就困乏了。因为肚子太饿了,我只好边走边要一路乞讨。不知挨了多少个日日夜夜我到了扬州。身上带的六元钱也无奈地用完了。口干舌燥,饥饿难忍。我想,何必饿死呢?哪怕被人打死也好。于是,在一天夜里,我进入一户人家,大摇大摆地打开厨房的碗柜,发现里面有吃的东西,我将声音弄得很响,就大吃起来,心想做个饱死鬼,人家发现肯定会打死我的。结果等我吃完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很扫兴地离开了。
等到了南京我已饿得头昏脑胀全身无力了。见到在南京工作的一个同学赵燕翔,他对我骑自行车到南京的事感到非常的惊讶。因他了解我的家庭情况,想留我与他同住。但我不忍心给他本身就微薄的生活再雪上加霜。于是我就离开了同学,打算到安徽九华山做和尚。只因人家要求的是大学生,所以我只好在南京谋生。
南京有个香蒲营,是保姆市场,其实就像奴隶市场,它刚好和人才市场相反,自己没有权利提出工薪和条件。如果有人挑中了你开个价,愿意就跟着走,当你说“不”的时候,广场其他的打工仔就会蜂拥而上。所以纵使有十块钱的工薪也会被人抢光。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推着自己的自行车站在那儿,想给自己一次谋生的机会,终于有一个人,原意付五十元薪水雇用我。
是做卤猪肉行当的,每天劈猪头,刮猪肉,虽然干活比较辛苦,但总算有个安身之处。可是,事与愿违,一个月后,老板因涉嫌拉嫖,趁夜深时他们夫妻二人就一起逃走了。老板丢给我一桶熟肉,说给我抵工资。在深夜我用火锥挑着一桶熟肉乘黑就往燕翔那里去,想明天卖点钱,正想着,“噗通”一声,脚下绊了一跤,一桶肉泼出去很远,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将肉块捡到桶里,心想这肯定没人买了。于是,我因走路困乏,就将一桶肉放在一家楼梯下,我也躺在那里睡着了,凌晨离开时,就将肉丢下了到燕翔那里。燕翔也为我伤心难过,挽留我,让我和他一起生活。但是,我知道他刚刚找到工作,生活费不够两个人的,就和燕翔告别,朋友一再挽留,我还是走了。
茫茫人海路,灰色迷蒙,我往哪里去?家实在不想回,那里有尖酸刻薄的怒骂声;那里有用眼角看我嘲笑我的一群人;那里有我不愿看到的忧伤痛苦以泪沐浴的母亲;我铁定心意,走吧,“我的路在远方……”
我怀着无比悲愤复杂的心情,用八块钱买了一张到砀山的西行火车票,踏上了不归的流浪旅程。火车漫不经心地晃悠着,心早已像死灰一般的冷漠和平静,什么也不能,也不想思考。我到哪里停车,就连自己也不知道。
无家可归的人哪!你往哪里去?哪里是你的家?
我眼望窗外,看到一座座的崇山峻岭,意味着我已远离生我养我的家乡不知多远了。我想起了早逝的父亲,泪如珠串,父亲啊!你可知,因着你不顾我们独下九泉,才使我漂流在外孤苦无依!死啊!你从何而来?我又想起老泪纵横的母亲,娘啊!这辈子也许我再也见不到您了?这段时间你脱离吵架了吗?娘啊,你太苦了,可是,儿子却离您越走越远了……
列车继续地往前行,我往何处去,我自己也不知道,买的车票早就坐过了站。不知不觉已是第二天了。
天上不见阳光,阴云密布。我身上的衣服有些单薄,似乎有些打颤。车上的人正热火朝天,我却感到格外的冷。细看窗外,已经飘起了雪花,原来列车已行驶在河南省境内。
我往哪里去?何处是我的归宿?这时广播里说了一句话“检票即将开始”将我猛然惊醒,我八块钱坐到现在。正好火车到了一个小站停车时,我匆忙地下了车。
寒风刺骨,鹅毛大雪覆盖着整个小站。这是河南省义马市。地上的雪已半尺多厚了。我卷曲在站前一户屋檐下,可是越蹲越冷,还不如往前赶路。夜如此得深,陪伴我的只有那被踩的“咯吱咯吱”响的大雪。路上没有一个行人,火车的鸣笛声划破夜空,显得格外得凄厉寒心。啊,人哪,为什么活在世上?
雪还在下,西北风还在呼啸,等到天亮时,我的头发结成了一个冰帽,身着雪衣。在白皑皑的遍地上,我看见远处山壁上有一个乌黑的洞口,不管有没有危险,赶紧躲进去。啊,里面真得暖和多了!我回到了古代“山顶洞人”的生活。
半斤多的老鼠成为我的同伴;我躺卧在路人的干粪便铺的地上;但是,饥饿的感觉无法抗拒,肚皮贴在后背上,有时浑身发烧,口干舌燥只好大口大口地吞食白雪。几十天下来,已经是浑身发烫,头昏脑胀,已快临近死门,没有人到洞里给我一口水,自己的尿水也成了唯一的救命源泉。
几个月下来,我已经面目全非,衣衫褴褛。在洞中,也不能穿衣服,虼蚤布满衣服,咬得你奇痒无比。又不想乞讨,只在夜里出来到田地里、菜场拾点烂东西吃。
偶尔出得洞来,就会像猴子被人玩耍,但我也没有了反抗和情感。我的神智开始混乱,但里面清楚自己是人,外面已经看自己不是人。
1990年的我,头发披到肩上,指甲长如鹰爪。我的嘴也绝了人话,在山顶上学牛羊吃草。有时向人乞讨,十次有九次被痛打或狼狗驱赶。
接着,我开始了继续西游的旅程。我开始沿铁路西行时,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鼓励我活下去,要我“就近找活干”。我说:“谁肯接纳我?”(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苦难中天父的保佑)我茫然地继续往前走。忽然,迎面走来一老汉停在我面前问我:“小伙子,想找活干吗?”我求之不得地答应了他。因很长时间没有人搭理过我,我就对他格外亲密,认他作干爸。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