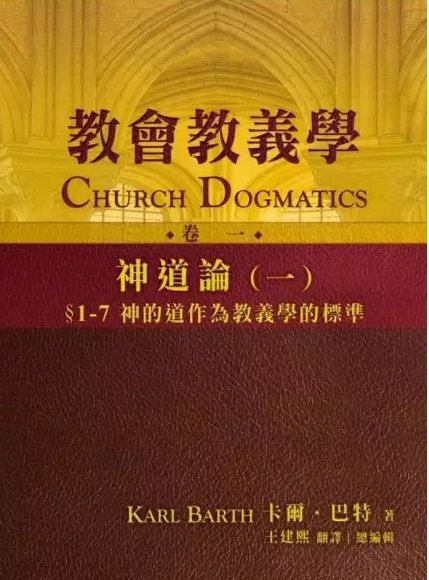编者按:本文是浙江大学曾劭恺教授为王建熙中译、天道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巴特《教会教义学》中译本所写的推荐语,本平台蒙作者允许转载。文后有作者附注。
瑞士神学家卡尔巴特无疑是基督教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近数十年来,巴特学在德语、英语世界方兴未艾,已然成为一门显学。单就学术研究出版数量而言,每年相关专著、专文可谓汗牛充栋,仅有奥古斯丁、汤马斯、路德、加尔文研究等领域足以与之分庭抗礼。而四卷《教会教义学》之于巴特的神学,犹如阿尔卑斯山脉之于瑞士的国土,或九大交响曲之于贝多芬的音乐般显赫。翻译如此巨著,无疑是艰巨的工程。王建熙博士的心血,在华语神学史上是个重要的里程碑。
事实上,阅读这样庞博的著作,也相当具有挑战性。就像马勒九首交响曲,必须是对音乐已培养相当程度理解与品味的人,才能静下心逐一细细聆听,巴特的《教会教义学》也属曲高和寡的作品。这部著作就如杜斯妥也夫斯基那些冗长艰深且时而枯燥的小说般,津津乐道的人不计其数,硬著头皮读完的人却不多。
然而笔者相信,只要读者愿意付出努力,一旦熟悉了巴特的神学思维及语言,必定能从中得到丰盛的收获,享受这部巨著,甚至欲罢不能。就连美国基要派神学家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虽视巴特如宿敌,却也是英语世界最早通读巴特著作的诠释者,且难掩他对这位神学巨人深深的钦佩与仰慕。巴特访美后,范泰尔在一封1965年寄给巴特的信件中写道:“当我终于在(普林斯顿神学院)的走廊上来到离你不远处时,有人让你注意到我就在左近,而你满有恩惠地与我握了手,对我说:‘你说了一些关于我的坏话,但我原谅你,我原谅你’,那时我受宠若惊而不知如何作答。”
笔者的导师杭星格(George Hunsinger)教授曾将《教会教义学》比作法国的沙特尔主教座堂(Chartres Cathedral)。初入这座大教堂的人,双眼需要一段时间方能适应较为昏暗的环境。然而一旦目光适应了环境,繁复的建筑、装置、艺术作品、彩绘玻璃,会令人目不暇给、叹为观止;每个细节都值得细细品味,而整体的结构又如此宏伟。汉语读者或许会联想到苏东坡笔下的庐山西林壁,或是北宋院画大家郭熙眼中的山水:“山有三远:日山下而仰山巔,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不论是苏軾眼中的西林壁、郭熙眼中的山水,或是沙特尔的主教座堂,视觉对环境的适应,乃是欣赏并赞叹这些奇景的前提。
同样地,《教会教义学》这部移步易景的著作,初读时也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倘若读者一开始觉得枯燥难懂,不需感到挫折。笔者曾与一位哈佛大学座席教授交谈,他是学术地位崇高的哲学家,而就连他亦坦言,读懂巴特的著作,对他而言极具挑战。巴特结合古典基督教神学术语以及现代德意志哲学用语,其思想表述一层层的辩证含意,若非抽丝剥茧般细细体会,则难窥其精妙之处。他的瑞士背景使得他的德文带著一种较为古雅的修辞方式,而环环相扣的子句在在显示他思想的复杂程度。
笔者初次阅读《教会教义学》时,曾花了足足一个小时,才读懂其中一个长句。当时笔者在爱因斯坦生前经常造访的冰淇淋店,一面喝咖啡,一面咀嚼这句话。终于读懂时,才发现冰淇淋已融化在桌上,咖啡也早已凉了。试图理解那句话时,心中着实苦闷,然一旦豁然开朗,那股雀跃却是难以言喻。
当然,笔者以学术神学为业,专攻巴特研究,而并非所有人都以学术神学为使命,也并非所有职业神学人都以巴特思想为主要兴趣。然而但凡有意钻研神学的读者,就算完全不读巴特,也不可能避开他的影响,就像王羲之的字体之于研习书法的人一般。莫特曼的盼望神学、耶鲁学派的叙事神学等当代教义学路线,皆是在巴特身影下萌芽生长。巴特也启发了教父学、宗教改革神学研究、现代神学研究等历史神学领域的许多范式。透过与巴尔塔萨(Hans Urs von Balthasar)等人的对话,巴特也成为天主教“新神学”(Nouvelle Théologie)学派当中巨大的身影,而当代英语巴特学界屈指可数的泰斗,也包括了天主教神学家莫纳尔(Paul D. Molnar)。在新约领域,赖特(N. T. Wright)的“批判实存主义”深受巴特影响,尽管他自己几乎未曾明言,或者他可能并不自知。旧约研究方面,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的修辞批判学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许多巴特所树立的神学方法论,这可见于布氏的“法庭与见证模型”、辩证法等。巴特的三一神学,亦是当代更正教与东正教对话的重要桥梁。甚至在犹太教神学界,巴特亦占有一席之地,他对旧约的诠释,为舒弗艾斯(Harold Schulweis)等犹太拉比带来了重要的启发与挑战。美国福音派近年来所辩论的“圣子永恒从属”(eternal subordination of the Son),在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某种巴特三一论的变异。
笔者与好友洪亮经常强调,我们都不是巴特主义者。然而,研究巴特除了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过去半个世纪西方神学整体发展脉络的主轴,更能为我们在自身信仰的反思上带来许多启发。譬如笔者并不接受巴特在《教会教义学》I/1当中关于上帝话语三重形式的论述。笔者相信,圣经是圣灵默示的命题启示。然而,正如福音派圣经神学之父霍志恒所言,圣经命题启示的内容,并非机械式的条目,而是又真又活的历史──上帝在基督里的救赎历史。圣经又真又活的历史性,正是巴特反复强调的重点,而就算读者对于圣灵默示圣经的方式采保守的理解,仍旧能够从这重点获得重要启发。
此外,《教会教义学》的书名,对当代华人教会某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是极为重要的提醒。许多信徒坚持“唯独圣经”及“圣经的清晰性”时,带有一种误解,以为宗教改革的信仰,是一种“去教会化”的信仰:每个信徒只需自己读圣经,即可建立对神的正确认识。曾有一位华人名牧,在讲坛上公然教导古代的异端,却高呼“我不在乎大公信经怎么说,我只在乎圣经怎么说”,而这在美国福音派的新约研究当中,似乎也已成為一种相当普遍的态度。对信经、历代大公教会正统的忽视甚或轻视,是当代华人教会及部分美国福音派的一大通病。这种态度并不符合圣经明确的宣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三15)。
巴特在德国明斯特(Münster)任教期间,曾以《基督教教义学》为书名,开展了教义学的写作计划,且完成了导论(Christliche Dogmatik im Entwurf)。关于巴特放弃这计划的原因,至今在学界仍有辩论,不过他自己在《教会教义学》I/1的序言中,写下了一段令许多读者铭记在心的话:“我在书名中以‘教会’一词取代‘基督教’,乃在于试着树立自我约束的良好榜样,不随意使用‘基督教’这伟大的词……”
任何神学家都可以称自己的神学为“基督教”神学,但脱离了教会的规范,基督教还是基督教吗?除了教会,基督还有别的身体吗?巴特强调,神学乃是属乎教会的学科,而任何神学人若试图在教会正统的规范之外诠释圣经,至终必定偏离圣经所见证的真理,即神在耶穌基督里的自我启示。且不论巴特自己对信仰的反思,以何种方式、在何程度上受教会正统及圣经的规范,《教会教义学》这书名在现今个人主义挂帅的时代,诚然尖锐地提醒我们: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必须站在历代圣而公之教会这伟大巨人的肩膀上,并受教会正统的规范。
一言以蔽之,笔者以为《教会教义学》是所有愿意深入思辨信仰的基督徒(或者愿意深入理解基督教思想的非基督徒)不可错过的巨著。笔者可笃定地说,一旦找到进入文本世界的钥匙,开始在阅读的过程中与巴特摔跤、受他的挑战与启发,必定会为任何读者带来丰盛的收获。
【作者附注】
天道之前发布了出版巴特《教会教义学》I/1 中译版的海报,海报上引用了我推荐文中的一段文字作为荐语,到今天已经有许多人私讯找我,提出相关疑问。
这些问题基本上不外乎“巴特不是新正统吗?”、“巴特的神学不是有问题吗?”。当然,会私讯找我的都是朋友,所以都很友善,甚至可以说都是以愿意聆听并且学习的态度提问。但我也听说许多人以非常强烈的敌意看待天道出版巴特《教会教义学》的决定,以及我在海报上的荐语。
不过,就连那些善意的问题,也反映了华人教会一种相当普遍的反智倾向(我不是说那些提问的朋友反智,而是说他们在这样的教会处境中习惯了某种提问的方式):不去问“巴特说过什么”、“巴特怎么说的”、“这样说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而只是问“有没有问题”。换言之,这是一种“只论立场,不愿思辨”的倾向。
“新正统”是个很方便的标签,贴在巴特身上,就可以直接辨别他是敌是友。问题是,那些说“巴特是新正统”的人,究竟明白什么是“新正统”,又明白巴特的论述吗?
“新正统”是个具有确切定义的专有名词,专指一个特定的二十世纪神学流派,又名“辩证神学”、“危机神学”,属于一种基督教存在主义。巴特早年跟这圈子走很近,但1920年代就渐行渐远,1930年代正式开始反对这流派的思想。他在I/1序言中明确跟“辩证神学”划清界线,并在III/3序言中强调自己不是“新正统”。巴特的神学自早期至晚期都使用辩证法,但这不代表他属于“辩证神学”;他视圣经為历史对启示的“见证”,这也不代表他是“新正统”。
康牧师当年鼓励我去研究巴特时,曾对我说:去把巴特哪里讲得好、哪里有问题,都研究清楚,不要不清不楚地定他罪,却处处受他影响而不自知。当时港台教会受了巴特很深的影响,却又不明就地视之如蛇蝎;对“新正统”这品牌避之惟恐不及,却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仰赖它的产品。
不论如何,以上是我推荐文的全文。读了以后,就可以大概晓得为什么我要推荐这部译本了。
京ICP备07014451号-1 | 京公网安备11010502025431© 福音时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