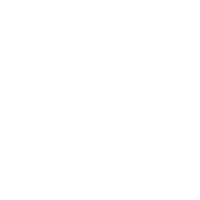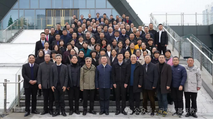我已老年却常想念童年的野台戏,更想寻找一种快消失殆尽的民间情调。“野台戏”也叫“平安戏”,戏台上诉说的就是人人心中的平安,祈求生活多一些喜乐,不论你求的庙神还是我求耶稣基督。
过年过节人人就像穿上谦卑的衣服,愿意放下自己,愿意彼此服事,做神所喜爱的孩子。
现代生活不愁吃穿,固有的节庆对许多人来说形式大都免了,愈来愈只剩下印象而已。童年记忆中的“平安戏”,它最足以代表“过年”:广场四根大木柱搭起临时戏棚,回荡的锣琴,对照广场无所不见的四字“神爱世人”——它在戏台大柱子上,在橄榄树上,在大石壁上,我看它才是什么也无法取代的年味!如今春节更让我反省生活的真义: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得前书3:3-4)
每年年关,石壁潭村民就开始认真地忙碌准备神事和搭戏台。人们看戏了,山歌也唱了,各自向自己的神祈求后,这才算过年。记得不远处仍见广场建筑的廊柱上贴着“神爱世人”。
过大年夜,孩子们屈缩在自己的家里拿红包、搓汤圆、摸四色牌,只觉得全世界的气氛都闹热滚滚,外头广场上的戏棚子早已搭好,也总看见有人在橄榄树上悄悄贴上“神爱世人”四字。孩子们就等第二天天亮时拿着压岁钱买广场上小贩的仙楂、棉花糖和烤鱿鱼……虽然屋外院落中正流窜着冷冽的寒风,但有说不出的期待和兴奋。除此,年味还在百岁榕树的龙须下,在戏台四大柱前枱挂的小黑板写的戏码中,在九腔十八调的客家山歌中,还在老祖母看戏坐的旧藤椅里……那里头更有节庆,那里头有更浓的年味。如今老祖母已远去天家卅年不止。
记得平安戏总是年味最高的兴奋点,琴师调音的声音,不时来一段“奇异的惨伤”,伴着“风急天高”的调子。在广场旁的百年榕树须垂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是村民期盼好戏上场的脸;村民们瑟缩在戏台前,通常我们早已替老祖母拿了一张老藤椅,占好她每次都坐的老位子……
我仍想念客家小村,沐浴村民的礼赞。平安戏给我印象最深,因为我住的风城总流窜大风,不论戏棚下或老祖母的老藤椅里都有强风。戏落幕后,我们还要唤醒正打呼噜的老太太,但是次日问及前晚夜戏剧情,她从没蒙混说错过……那种认真与虔诚,大概因为从年轻看到老的戏码不外乎那几出?上戏前她只要知道戏码,就对剧情如数家珍倒背如流,因为老祖母几十年来已看无数次了。
我也从老祖母处学得下午多武戏,就是肢体互动武打较多,不论良臣勇相或千古枭雄,多是忠义故事;晚上多文戏,通常口白对话较多,文戏除有文生武将,更多丑旦、花旦或苦旦的唱腔与扮相都美。我印象最深的是平板及山歌子两个曲调,因为都是四四拍子,歌唱时一字一拍的唱法通常会有空隙,所以演员发挥就更活泼生动,可以自由添加成为长短句,花旦及小丑常唱山歌子,小生及蓝衫苦旦则多唱平板。
平安戏中最受村民欢迎的仍是情爱故事,有洒泪的也有幽默笑料。一个夜晚两小时绝无冷场,戏台下的村民就跟着台上有时生旦后花园私会,有时公堂审案,有时击鼓喊冤,有时酷刑问斩,有时暗地相思……有人爱任侠少年,有人爱一丝柔媚,一颦一笑,唱念做打都牵动台下观众的眼神。
还有一个视觉印象很深刻的是戏棚上那一大块帐幕,它把前台和后台区隔开来,前台可三面观戏。那一大块布幔总画有鲜艳牡丹,后来客家老人总这样说:“我们是来自中原的子弟!”于是记忆中布幔里的中原牡丹就成了我心中的客家精神,在晴耕雨读中流露着雍容华贵的牡丹风华。
“野台戏”在民间小村常有不同的说法,有人称它“平安戏”,或“大戏”,或“收冬戏”,或“采茶戏”,甚至也有“二月戏”。客家人多务农,稻子一年收成两次,农民的晚稻收割入仓后,为庆祝一年平安无恙收成丰硕,就由地方人士或庙方共同出资,邀请传统客家剧团到广场演出,筹神献演时顺便宴请亲友。戏棚上的华丽与演员的演技比起当时黑白电视戏剧绝对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客家平安戏能坚持一路演下来,看得出来自中原的客家子弟,血脉里隐藏着狂歌,从五胡乱华一路南迁,积累了一千五百多年来的乡愁,它不同于海盗,更与山贼迥异,人人心怀感恩与怀旧,更展现客家人晴耕雨读的勤劳、自由与爱!人人靠近神时,心志笃定不变:“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欣。”(诗篇5:11 )
尽管年节戏味早已不足,但逢年过节时仍想到戏台下凑个热闹买串山楂,向神讨讨平安,分分喜乐。有时我不禁想:也许时代变得太仓促,也许传统走得太匆忙,但我还算是正宗的客家人吧。
虎年要到了,笔者为所有中国人祈福:“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啊,我要歌颂你的名!”(诗篇9:2 )
阿们。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北京一名基督徒。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