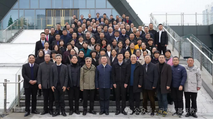基督教中国化并不是要让基督教回到古代中国去,穿上中国的古装,因为基督教中国化更接近于“基督教处境化”,只不过那个特殊的处境便是“中国国情”。在当下特殊的中国国情下,基督徒怎样来发展教会的事工呢?基督徒还能像从前那样传福音并开展各样相关的工作吗?
以前的福音工作也就两大块,一块是宣教或户外布道,另一块则是培灵聚会,这两者在当前形势下都出现了较大的困难。一方面因为是宗教政策的限制,另一方面则是疫情的影响,尤其是培灵聚会,自从武汉出现疫情后,笔者没看到周边教会举行过培训大会。但是,在笔者看来,多媒体及小组事工的普及不就是基督教中国化在牧养事工中的体现吗?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已经汗牛充栋,笔者也不想重复已经出现的观点,在此谈一下基督教中国化大背景下小组事工该如何深入进行。
一、基督教中国化在牧养领域的体现便是向纵深方向发展
对基督教中国化的理解可以聚焦在如何解决“中国化”这三个字上面,可以将“中国化”理解成“中国方案”,就如有关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基督教是普世性的宗教,基督教中国化并非要让普世性的宗教变成被地方局限的宗教,而是要突出“中国化”的普世性贡献。换言之,中国化的目的是要让基督教在中国文化的浸润下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为普世人类做贡献。
基督教中国化不仅是基督教处境化,也是基督教的本色化,要突出中国文化的积极一面。在过去,人们尤其热衷于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但现在,不少人开始意识到“道家”的“法自然的”自然主义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老子所注重的“柔弱之道”便是最佳的例证,正所谓“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也”。在这种思维模式的指引下,我们会更容易理解“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因疫情的缘故,不能进行培灵会并不一定就是件坏事。神关了一扇门,会为我们开另一扇窗,小组事工就是很好的模式。因为它更加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也符合时代的特质甚至圣经的教导。即便我们今日因着种种限制处在“软弱”之中,但“弱者道之用也”,如果我们能放下负面情绪,甘愿接受这种限制,并且让这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那么也许就能结出许许多多的子粒来。我们若接受这样的限制,仍可以在这种限制下成长,因为我们可以将福音的事工往纵深方向发展。
二、不要追求过快扩张,而要注重沉淀性的工作
小组事工是一种化整为零的事工,让教会在这无声无息的过程中悄然建成主的灵宫。既是如此,我们又该怎样运作此项事工呢?该怎样运才能使教会往纵深方向发展呢?小组的模式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极具处境性与灵活性,是一种可以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事工。即便这项事工是一项从海外引进的事工,仍可以对其进行本地化的处理。比如,我们要不要像韩国的纯福音教会那样,建立一个类似天主教的教阶制那样复杂的组织架构呢?在当前处境下,这种模式显然是不适合的。
首先,外部环境不允许我们发展出超级规模的教会模式,否则必会引发不必要的关注并带来额外的阻力。而且,以目前教会的资源来看,也不宜发展出超级教会的模式。因为一旦做出这样的决定,很可能会导致“无法完工”。毕竟,我们的资源很匮乏,平信徒的素质偏低,如果发展超级教会,就必须确保足够多的小组长、导师、区牧等能投入该项事工。假设在做出该决定前,只有100位可供教会差遣的侍奉者,那发展超级教会之后必须保证能产生数倍的组长及导师,这是比较困难的。
其次,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积淀及各样环境的历练。我们必须承认并不是每个信徒都具有成为组长及导师的潜质。如果我们不顾实际情况,让每个教会成员都往属灵领袖方面发展,反倒“适得其反”。前面笔者曾假设一个中型教会能提供100位可供教会差遣的侍奉者,但是,具体领袖潜质的可能只有10个。如果这样,我们就只能暂时准备开设10个小组,等到组长与导师的数量增多了,再将小组事工的规模随之扩大,两者必须同步进行。
在福音事工上有迫切的心是好的,但过于焦急、拔苗助长是不应当被提倡的。在属灵的道路上,从来没有捷径可走。我们必须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结果;必须流泪撒种,才能欢呼收割。如果单求外在的果效,却忽略了灵性上面实在的建造,必定欲速则不达。反之,如果我们能实实在在将小组牧养做踏实了,也许起初发展缓慢,但后面则将越有果效。
注:本文为特约/自由撰稿人文章,作者系浙江一名传道人,文中观点代表作者立场,供读者参考,福音时报保持中立。欢迎各位读者留言评论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