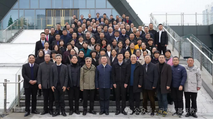摘要:本文选取宗教改革过程中马丁路德和慈运理之间的马堡会谈中对于圣餐的分歧作为一个切入点,分析他们分歧产生的内在原因,并从该历史事件和圣餐本身的意义之中思考圣餐与教会合一的关系。圣餐本为教会合一的象征与促进因素之一,但是宗教改革时,改教家却因为对圣餐问题的理解有分歧,而造成新教教会一定程度的分裂。中国教会正在建设中国化的神学,与改教初期相似,都处于要在大公传统之中建立自己小传统的转型时期。因此可以以史为鉴,思考该事件对于中国教会的意义。
关键词:圣餐 合一 宗教改革 马堡会谈
引言
2017年是宗教改革运动发起500周年。对于基督新教来说,宗教改革的重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宗教改革发生在过去,但并不过时。改教家路德、慈运理、加尔文等人的影响至今仍在。改教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依然对教会持续发生影响。本文选取宗教改革过程中马丁路德和慈运理之间的马堡(Marburg)会谈中对于圣餐的分歧作为一个切入点,分析他们分歧产生的内在原因,并从该历史事件和圣餐本身的意义之中思考圣餐与教会合一的关系。宗教改革时期教会改革和确立新模式,在此过程中,改教家们在探索的过程中难免有分歧。当前中国教会也在建设中国化的基督教,在教义、礼仪、组织等层面都需要在大公传统的基础上处境化,任务艰巨,虽然共识很多,不排除在细节上出现分歧。如何面对这些分歧,教会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妨加以留意。
圣餐和洗礼是基督新教所认可的两大圣礼,自改教之后,圣礼就成为基督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重要分歧之一。这两项圣礼由耶稣亲自设立,并嘱咐教会施行。按照艾利克森的定义,圣餐是“由基督自己设立、由教会施行、来纪念他代死的圣礼。”[1][2]教会普遍相信,圣餐象征着教会的合一。圣餐仪式的不断举行,应该更能促进教会的合一。根据艾利克森的观察,“虽然实际上基督教的每个支派都举行圣餐礼;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对它却有着许多不同的解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过去已经使、今天仍在使许多基督徒群体彼此分裂。因此,圣餐既是一个将基督教王国联合起来的因素,同时也是一个使之分裂的因素。”[3]以下就从教会历史中选择一个事件来体会艾利克森的上述观察,思考圣餐与教会合一的关系,从而认识到施行圣餐礼不但是教会的重要标记之一,也是维系教会合一的重要因素。
一、马堡会谈中的圣餐观之争
慈运理和加尔文是“改革宗的信仰之父”,和路德一起,都是“宪制的改教家,其改革是受到具有统治国家权力的行政官员的赞同,并实际得以确立的。”[4]后来的新教主要的宗派如路德宗、改革宗都受到这三位改教家的影响。
改教家的改革力度不可谓不大,他们废除了原来天主教七项圣事中的五项,只保留了洗礼和圣餐礼。当然,“圣礼没有被放弃,但现在他们同上帝的道——上帝拯救世人的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5]改教家们对于保留下的两项圣礼也有新的解释,而这些解释又不尽相同。路德和慈运理之间在马堡的会面非常清楚地表现了这一问题。
马堡会谈发生在1529年10月,当时支持新教的地区,面对反宗教各改革的天主教及其支持者,感到压力巨大,迫切希望可以建立一个泛新教联盟。然而一个巨大的障碍横在他们面前,这个障碍就像是隔断他们的一堵墙,这堵墙就是以路德和慈运理为代表的新教两大群体对于圣餐的不同理解。要缔结政治和军事联盟,一起对抗天主教,就需要首先在神学上达成基本共识。于是在黑塞的菲利普等人的推动下,马丁路德和慈运理等众多神学家齐聚马堡,商讨神学问题。
他们对15个神学议题中的前面14个问题都基本达成一致,却直到分开时,都无法对圣餐结成共识。对于路德来说,他无法接受慈运理仅仅把圣餐看做是纪念的观点。路德虽然不完全认同当时天主教的“同质说”,但其实相比之下,他对圣餐的观点最接近天主教。
双方都非常努力地致力于沟通和理解。慈运理在分手时流着泪说:“在这个世界,我最愿意与他们成为一体的是维腾堡人。”[6]
不论在当时,还是今天,人们普遍为此感到惋惜,因为在那样紧急而为难的形势下,这次难得的会晤,没有达成信仰同盟,也没有军事和政治上的联合,留下的是分裂各自为战的新教。这次“会谈的失败为反对宗教改革一方之后一个半世纪里的胜利铺平了道路,至少局部上可以这么说。”[7]甚至可以说影响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势头。给天主教在局部地区的反攻和胜利提供了机会。
后人回头去看当年路德和慈运理之间的争端,可以发现,慈运理认为圣餐只是一种象征,纪念。在他看来,不论是原来天主教对于圣餐的观点,还是路德的圣餐观,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两种观点,都认为基督的身体和血在圣餐中与饼和杯同在。保罗在谈到圣餐时这样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林前11:26)圣餐确实是纪念性的,象征性的。慈运理“强调圣餐的作用就是叫人纪念基督为信他的人代死以及它所带来的功效。”[8]于慈运理不同,“路德则把圣子耶稣在伯利恒马厩的道成肉身同圣餐礼联系起来。在圣餐礼中,饼和酒事实上转化成了基督的体和血,路德并没有试图用理性阐释的语言去理解或表达这一神圣的奥秘,但它成了路德的敬虔的核心。”[9]二人的信仰经历,对于有关教义的思考,在圣餐这一主题上集中凸现出来很多差异。
路德和慈运理对于圣餐的理解有差异,但是若与天主教相对比,他们又会一致反对天主教对于圣餐的解释。天主教传统坚持的是“变质说”,他们认为,“变质说坚称饼和酒的偶性在祝圣的那刻没有改变,但他们的本质却从饼和酒的本质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10]天主教还认为圣餐中包含着一种献祭行动。[11]改教家们并不承认这些。
其实,路德和慈运理的分歧并不是在马堡会谈时才产生。他们在会面之前已经形成自己的观点。比如路德,他对圣餐的理解基本前后一致。马堡会谈之前,路德曾批评过他的同工卡尔施塔特(Karlstadt)所持有的对圣餐的理解。卡尔施塔特“否认基督在圣体内的真实临在”,并认为“当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时,仅仅指着自己的肉身”。[12]对此,路德明确反对,他在1524-1525年间写了一本著作《反驳来自天上的先知们》,批判卡尔施塔特的观点。
在马堡,路德明确反对慈运理的圣餐观。因为马丁路德一直都认为“如果领受圣餐,基督仍在面包(和酒)的形式下存在”。[13]马堡会谈之后,路德坚持立场,1544年,路德在其所著的《关于神圣圣事的简明说明》中,对于那些否认“基督在圣餐中临在”的人表示反对和批评。[14]
以上可以看出,路德和慈运理在圣餐问题上的分歧在于:基督的身体和血是否临在于圣餐的饼和杯中,若临在,又是以何种形式存在。二人的分歧最终聚焦在基督论上,他们“从讨论具体经文的恰当意思变成了讨论基督的身体在哪里。”[15]二人都赞同卡尔西顿会议的基督论,即基督是一个位格两种属性。但是路德“更强调位格的统一性”,慈运理“强调两种属性的不同”,虽然这样一来,他们都未背离正统的基督论,但是这一差异“加剧了他们在圣餐上的分歧”。[16]最终,两位忠心勇敢为上帝所用的教会领袖因着对圣餐的不同理解而分道扬镳,独立面对天主教。
二、反思圣餐与教会合一
很明显,在路德与慈温利之间,对于圣餐的理解存在分歧。这个分歧是否足以导致教会分裂呢?教会在此前的近一千五百年间,有许多次因为各种原因差点走向分裂,或者已经出现各种类型的分裂。
其实随着时间推移,慈运理的观点并未在新教甚至瑞士教会中成为主流,后来改革宗教会中主流的圣餐观来自于加尔文。路德的观点后来在信义宗中也有所调整。
改革宗认为,“基督临在圣餐之中,但并不是有形身体的临在。相反,他在圣餐中的临在乃属灵或动力的临在。……认为我们实际上是在吃喝基督的身体和血,这种观点是荒谬的。真正的领受圣餐者乃是在圣灵把他们带入一种与主的位格更亲密的关系中得到属灵的滋养。”[17]如此一来,加尔文并未完全继承慈运理和马丁路德任何一人的圣餐观,而是以圣经神学为基础,提出了他对于圣餐的观点。他不认为圣餐中有基督实际的身体和血存在,同时也不认为圣餐中的饼和杯仅仅是象征,而是认为基督以灵性的方式存在于圣餐中。“加尔文一方面保持记号与被表明的东西的分别,另一方面又坚持记号真真正正指向它所表明的恩赐。”[18]加尔文的立场看起来是在路德和慈运理之间的中间道路,麦格拉斯认为他也可能被认为是“在改教运动的这个关键时刻作出的权宜之计。但事实上,支持这种讲法的佐证很薄弱,加尔文的圣礼神学不是政治上的妥协,反而反映了他对人如何获得上帝的知识的理解,尤其与‘俯就’(accommodation)这观念有关。”[19]
如果深究路德和慈运理关于圣餐的争论,可以改变我们对于这次争论可能会有的想当然的看法。首先二人绝不是有意制造分裂,他们是本着对真理的理解和坚持,基于自己扎实的圣经神学给出结论。就好像马丁路德并非一开始就想要和天主教分离,制造教会分裂。在他心中,教会合一非常非常重要。其次,对于慈运理的圣餐观,不能认为他的圣餐观仅仅是“纪念”。慈运理自己是这样表述的:“通过这个纪念,上帝在他儿子身上表现出的所有好处都浮现在人们的头脑中。并且,借着这些记号本身,即饼和酒,基督自己也来到我们面前,如同从前的时候,这样,我们不仅能够用耳朵听到,也能用眼睛看到、用嘴巴尝到基督,灵魂承载着基督,而且又在基督里欢乐。”[20]这样看来,慈运理的圣餐观并非是简单的象征,而是认为其中有属灵的祝福。举行圣餐,让人们与基督连接,并且分享圣餐中属灵的祝福,在基督里的欢乐。这样的理解不能看做是空洞的“象征”,也不仅仅是与基督面对面,而是分享基督的身体,与基督合一。其实,他的观点和路德、加尔文都有相通之处。虽然在慈运理时期的苏黎世教会,一年四次举行圣餐,但是他们同样在此圣礼中“宣告主的死亡并为他作见证,因为他们是一个身子中的肢体,他们是一个饼。”[21]
合一是教会的重要特征,也是教会追求的目标和坚持的原则。正如梁家麟所言,“不管我们持守怎样的神学立场,总不能否认合一是基督教的重要思想,亦是圣经对基督徒的一项要求。”[22]正如前文所言,圣餐本是教会合一的象征之一,也应该可以促进教会合一,然而事实上,教会也曾因着对圣餐的理解不同而有分裂。有时难免事与愿违。
回溯改教时期的教会历史,可以更清楚的感受到新教为何会走到今天这样的宗派林立,因为宗派问题伴随着新教的始终。宗教改革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组织的运动。
教会在古代也曾面临由教义或者礼仪等问题导致的分歧,进而可能走向分裂。多纳图派问题是这一类问题中的典型。对于多纳图派,奥古斯丁曾经明确表示,教会最重要的特质是爱而不是圣洁,因此,合一是教会最基本的特征之一,主张分裂者就是异端。[23]合一曾经处于在教会主流意识形态中非常被重视的地位。奥古斯丁的教会论在教会中影响极大。以致于有人这样评价宗教改革,“从内部考虑,宗教改革运动只是奥古斯丁的恩典教义最终战胜奥古斯丁的教会教义而已。”[24]改教家们在奥古斯丁的思想中选择了真理优先于合一。
回顾过去,可以看到,虽然非常艰难,但经过历代教会领袖的努力,基督教正统被确立起来。当然这种状态的实现,从根本上看是基于上帝的保守和引领,从人的方面说,则是基于合一的圣经神学基础,教会体制的建立与维系,以及教会和政权的权力。教会始终认为真理只有一个,教会之外无拯救,并且把教会真理的诠释体系化规范化。就像梁家麟曾指出“真理即或只有一个,人仍会对之做不同的理解,很难达成一致的看法。圣经只有一本,但对圣经的诠释却是五花八门,言人人殊。所以,要教会维持合一,非在一定程度内诉诸权力不可。‘正统’一词,代表的不仅是真理,也是权力。”[25]教会正统的维系,需要教会在教义和组织等方面的努力,很多时候还需要政府介入支持。
宗教改革所导致的教会分裂,并不是没有先例。教会在历史上,曾经出现形形色色的分裂。最严重的莫过于1054年的教会分裂,让普世教会分裂为东正教和天主教,双方各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以及相对独立发展的阶段,分裂只不过是把原有的分歧表面化,分道扬镳之后,各走各路。与此次相比,宗教改革有所不同。新教是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来。改教者必须给自己合理化的解释。于是,“改教者必须坚持自己信奉的教义是唯一正确的,而坚持真理比维护合一更为重要。真理不容退让,惟有在对真理的看法相同的前提下,合一才成为可能。”[26]这无疑首先是出于当时的实际需要,否则,改教的合法性以及新教存在的合法性将面临严重危机。
对于合一问题,基督新教基本认为:“真理的相同才是最根本的,组织上的合一只属次要的考虑。”[27]这样的态度和古代教会对于合一的理解有明显差异。虽然为了追求真理的合一而不惜失去组织的合一,也很难说完全错误,但是由此导致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教会历史有足够多的证据可以说明维持真理的合一有多难,甚至有时似乎不可能实现。
到底什么是合一?教会想要怎样的合一?艾利克森归纳出以下四种对于合一的理解。[28]
第一种是属灵的合一,即普世教会圣徒相通,将来在某一个时间,作为基督新妇的教会聚集,才会实现真正的合一。这种观点不认为有形的教会能合一,或者不考虑这个问题。
第二种观点关注有形教会彼此之间实实在在的承认与相交。在坚持共同信仰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促进不同宗派或者区域教会之间在讲道、宣教等具体事工上的合作与配搭。
第三种观点提倡公会议的合一。即教会各自保持原有身份,以协会或者公会议的方式联结在一起。
第四种观点认为教会合一是机构的合一。按照这种观点,各宗派首先自己联合起来,最终所有的宗派联合成为组织上合一的教会。
从艾利克森的归纳可以看出,教会组织的合一,似乎不太被重视。有些基督徒关注教会属灵方面的合一,有的关注具体教会实践的合一。
教会所谈的真理,往往“集中在礼仪和教义的层面”[29]。可惜的是,在这两个层面,教会在过去的历史中从未成功过。即便是对于圣餐,新教各宗派的解释依然差异明显。
由于基督新教从起初就坚持真理优先,这给一些不愿意合一的宗派或者个人提供了机会。梁家麟曾指出,“先谈真理后合一,往往是拒绝合一的最佳借口。”[30]这样的一种预设和前提,也正好可以来解释艾利克森对于教会合一的观察——“这种在公会议及教会机构合一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后一种情形,在近些年以来出现了明显的衰落。”[31]因为对于新教来说,理论上没有把组织合一放在优先位置,事实上也从未实现组织上的合一,所以最终有形教会的有形合一,只能日益衰落。于是合一就成为信徒属灵的合一,在特殊情况下,也会有部分教会或者宗派,将属灵合一与具体的教会实践相结合。
教会传统中对于合一的坚持,对于教会组织制度上合一的坚持,对于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一直未出现强大的宗派主义现象是有帮助的。
教会中,“争议的主要范围在于教会合一的本质,以及圣礼。在教会体制的正确模式上,也有重大差异。”“罗马天主教教会宣称,教会的合一是有形及有组织的。它相信并教导,教会体制的唯一正确模式是教权制度和主教制度——即以在教宗权下的一群主教为核心。……根据罗马天主教的信仰,在其历史及教权制度之外,并没有耶稣基督教会的真行相。”[32]
追求教会合一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障碍,比如说,是否为了合一,就可以任意放弃自己的宗派传统,或者是为了避免分歧,就把各自观点模糊化。
中国教会在转型调整并逐步中国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和机遇。而从本文所论述的圣餐与合一的主题来看,可以得到不少启发。虽然中国教会已经进入后宗派时期,但不代表教会在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一致了。
天主教“坚持教会那可见的合一。这条原则足以压倒许多别的原则。新教人士虽然会重视教会的合一,但对于他们来说,福音的纯净毕竟重要得多。据他们看,教会的存在,在乎它是不是忠于那单凭信心靠基督藉恩得救的福音真理,过于它是不是维持着可见的、制度上的合一。……新教的原则往往优先过教会合一的愿景及与历史的基督教的伟大传统一脉相承的理念。”[33]
“基督徒之间虽然在有关教会与圣礼的信念上有明显差异,但他们一致相信,教会是由神设立,为神所保养的基督的身体、圣灵的殿,而在某个层次上,即使表面上看来并非如是,但它确实是独一、神圣、大公及使徒性的。所有真基督徒至少也都重视洗礼和主餐这两个圣礼或礼仪,虽然彼此对二者的意义及在施行的细节上存在争议。”[34]
基督教在教会观方面的立场非常明确:“教会是神设立的团体,基督藉祂的灵临在于教会中,教会基本上是独一、神圣、大公和使徒性的。新教人士倾向把教会的独一性和大公性,解释为是无形的,而不是制度上的,但天主教人士则把这些看作是在本质上与使徒统绪的主教制度,特别是与罗马主教作为教宗的传统分不开的。新教人士大体来说,把教会之承传自使徒理解为承接使徒的教导和传道的传统,而天主教人士就将之解释为主教制度的存在,承接使徒统绪的传统。新教人士在《尼西亚信经》宣认的四个教会标记之外,加上‘正确宣讲神的话语’及‘正确施行圣礼’两个重要的标记。”[35]
三、牧者的责任
圣餐礼中至少涉及主礼人、饼和杯,领圣餐的信徒,还有观礼的慕道友。举行圣餐时,需要“教会选出并赋予权力的人来监督并主持圣餐崇拜的服侍”[36]。这个人往往是牧师,教会的牧者。冈萨雷斯曾评述初期教会领袖西普里安的观点:“教会的合一在于主教制,所有主教在其中都有一份,犹如共有的财产。合一并不是外加到真理之内的东西,反而是基督教真理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若是没有合一,也就没有真理;除了合一,就没有救恩;除了合一,也没有洗礼、圣餐或真正的殉道。然而,这个合一并不包括臣服于一位‘众主教的主教’,而是在于所有主教之间的共同信心、爱心与交通。”[37]也就是说,“西普里安郑重地主张,教会的合一在于主教的团契。”[38]奥古斯丁也在多纳图派争端中指出教会合一的重要性。如果说初期教会的主教及主教制有力捍卫了教会的合一,那么今天中国教会的牧者也应该为捍卫教会合一作出应有的贡献。牧者的合一将为信徒的合一作出榜样,为教会的合一提供基础。
“合一是成熟的其中一面。合一是抗拒对不够理想的事情不耐烦的试探。”有形的地方教会一直都会有各种不理想之处,怎么办?“解决的办法不是分裂,以为可以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创造理想。现在,分裂仍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解决的方法是继续活在现实中,同时注视着理想,朝理想努力。”[39]
“事情分为两种:现实和理想。成熟就是看见理想,并且活在现实之中。失败就是接受现实,拒绝理想。只接受理想而拒绝现实,是不成熟的。不要因为看见理想而批评现实。不要因为看见现实而拒绝理想。成熟是容忍现实,但坚持理想。”——普林斯 Derek Prince 因此对于我们教会的牧者来说,成熟的做法是,凭着信心,看见在未来,天上的教会是完美的,理想的,同时又能容忍现实教会的不完美,在现实和理想的差距之间,依然有信心、有盼望。
恳求上帝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圣经中一共有六次直接提到“合而为一”。在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一连四次提到合而为一,吩咐门徒要合一,天父赐给基督的荣耀,他已经赐给我们,并且要门徒合一,像圣父与圣子合一一样。基督已经为我们祈求,让我们合而为一。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2:14节所言,基督使我们和睦,祂也是我们的和睦。基督是教会的头,也是教会的和睦。上帝也会拆毁教会之间、宗派之间隔断的墙,让具体的地方教会内部合而为一,让教会之间合而为一。
“神是三而一,却仍然是合一的。这正是三一神的本质。”[40]上帝三个位格的合一,成为教会合一可以效法的对象,教会的合一,“是三一神合一的副产品”[41]。这样一种理解把三一神的合一与教会的合一联系起来。对此,斯托得的评价直截了当,他说:“教会的合一好像神自己的合一那样不能破坏。要分裂教会,就好像要分裂三一神那样不可能。”[42]
牧者要和睦相处,这有助于教会合一。教会要合一,“前辈必须挤掉骄傲。骄傲是那么隐晦和普遍,所以需要彻底的行动,将它连根拔起。由种族、传统、家庭、基督徒经验和知识而来的骄傲,都会形成陷阱,我们一旦跌入这个陷阱,就会导致教会分裂。”[43]“我们往往宣称,分裂是源于属灵的原因,实际上却经常只是因为性格或文化的因素。……与文化无关[44]的是,圣经要求教会合一。”[45]
蒂德博尔警告说:“有一个源自神的分裂,便有十个不合神心意的分裂。虽然我们宣称自己追求圣灵里的新生命或教义的纯正,但导致分裂的最常见原因,就是我们有罪的性格,以及我们不愿意寻求圣经里这种强调爱和合一、难以达致的圣洁模式。”[46]
牧者对于维护教会合一,反对教会分裂,理所应当负有更大的责任。
现代主义重视传统和权威,后现代主义则相反,消解权威,认为一切都是相对的,多元主义是其特征之一。然而“信仰本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抉择”,“一旦有人对信仰采取一种无所谓、兼容并蓄的态度,那肯定再无任何信仰对象或内容是与他们的生死祸福攸关了”[47],“从个人信仰层面说,宗教信仰却一定不能是多元主义或者相对主义的”。[48]
结语
作为当代中国基督徒,我们该如何面对基督教传统,如何回应中国化的方向呢?邓瑞强曾这样提醒我们,“无论如何,一个真实的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总是按‘传统’的指引去‘看’,并大胆回应上主的呼唤,从‘传统’跳向‘将来’。……立足于坚实的‘传统’,透过‘传统’提供之‘见’,大胆地迎向‘将来’种种问题的人,才算是‘历史’地‘存在’过的人。”[49]
当今天的教会反思宗教改革时,也不应忘记楚门的提醒,他说“宗教改革代表一种运动,也就是将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教会生活与思想的中心。”[50]。在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过的教会一直需要改革,需要归正,不断把“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置于教会生活与思想的中心。”中国教会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依然需要将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价值继承发扬。
传统非常重要,“人所站之处,就是其‘传统’。有了‘传统’,才有‘越出’自己的据点。……没有‘传统’,我们根本无法‘存在’。”[51]然而神学在发展,传统不断被更新。从慈运理到加尔文,圣餐观在不断更新,有继承,有发展。当今教会继续需要像改教家那样处理过去、现在、未来的关系,处理传统与更新的关系。对于基督徒而言,也需要实现生命的饿跳跃,所谓“生命的跳跃,就是由所占之处跳到未得之地,所站之处是人的‘过去’,未得之地是人的将来。由过去到‘将来’,开展了有意义的历史。”[52]
借着圣餐礼的施行,信徒与基督相连,与基督有份。借着“在基督里”这样的关系,所有神的儿女合一。圣餐礼不但提醒我们纪念基督为我们代死,等候主再来,也是在提醒教会,不论是牧者还是信徒,都是互为肢体,同为神家里的人,为什么不能合一呢?
每当教会举行圣餐的时候,不论他们多久举行一次,不论他们在细节上是否略有差异,所有的人都应该思想基督要求合一的命令。
“圣餐象征着教会里信徒之间的合一,以及他们彼此间的爱与关切。圣餐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身体只有一个。”[53]分别为圣不是把其他的主内肢体分开,只留下自己与基督,这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不符合上帝的心意。
那为主被囚的使徒保罗劝所有蒙召的人:“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54]愿我们如此行,“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55]。
[1]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0页。
[2]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0页。
[3]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0页。
[4] 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5]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6] 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0页
[7] 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130页。
[8]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3页。
[9] 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9页。
[10] 麦格夫(Alister Mcgrath):《历史神学》,赵崇明译,天道书楼,2002年,第242页。
[11]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1页。
[12] 《毕尔麦尔(Bihlmeyer)等编著:《近代教会史》,雷立柏(L. Leeb)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13] 毕尔麦尔(Bihlmeyer)等编著:《近代教会史》,雷立柏(L. Leeb)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14] 毕尔麦尔(Bihlmeyer)等编著:《近代教会史》,雷立柏(L. Leeb)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15] 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 132页
[16] 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
[17]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2页。
[18] 麦格夫(Alister Mcgrath):《历史神学》,赵崇明译,天道书楼,2002年,第246页。
[19] 麦格夫(Alister Mcgrath):《历史神学》,赵崇明译,天道书楼,2002年,第246页。
[20] 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21] 蒂莫西·乔治(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22]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明风出版社,2012年,第338页。
[23]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明风出版社,2012年,第339页。
[24] B. B. Warfield, Calvin and augustine, Philadelphia, 1956, p.210. 转引自阿利斯特·麦格拉斯(Alister Mcgrath):《宗教改革运动思潮》,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90页。
[25]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明风出版社,2012年,第339页。
[26]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明风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27]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明风出版社,2012年,第340页。
[28]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9-470。
[29]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明风出版社,2012年,第340。
[30]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明风出版社,2012年,第340。
[31]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0页。
[32] 奥尔森(Roger E. Olson):《统一与多元的基督教信仰》,李金好译,基道出版社,2006年,第276页。
[33] 奥尔森 奥尔森(Roger E. Olson):《统一与多元的基督教信仰》,李金好译,基道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34] 奥尔森 奥尔森(Roger E. Olson):《统一与多元的基督教信仰》,李金好译,基道出版社,2006年,第284页。
[35] 奥尔森 奥尔森(Roger E. Olson):《统一与多元的基督教信仰》,李金好译,基道出版社,2006年,第273页。
[36]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5页。
[37] 转引自罗杰·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4页。与冈萨雷斯该著作的中文译本略有差异。参冈萨雷斯:《基督教思想史》,陈泽民等译,金陵协和神学院,2002年,第204页。
[38] 罗杰·奥尔森:《基督教神学思想史》,吴瑞诚、徐成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9页。
[39] 灵巧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J. Tidball):《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陈永财译,基道出版社,2004年, 360页
[40] 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J. Tidball):《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陈永财译,基道出版社,2004年,355
[41] 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J. Tidball):《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陈永财译,基道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
[42] Stott, The Message of Ephesians, 转引自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J. Tidball):《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陈永财译,基道出版社,2004年,第360页。
[43] 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J. Tidball):《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陈永财译,基道出版社,2004年,第354页。
[44] 原文如此,加粗表示强调。
[45] 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J. Tidball):《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陈永财译,基道出版社,2004年,第358页。
[46] 德里克·蒂德博尔(Derek J. Tidball):《灵巧好牧人:牧养神学导论》,陈永财译,基道出版社,2004年,第347页。
[47] 原文加粗。
[48] 梁家麟:《基督教会史略——改变教会的十人十事》,明风出版社,2012年,第172页。
[49] 传统更新 “序言”第viii页。
[50] 卡尔·卡尔·楚门(Carl R. Trueman):《宗教改革:过去、现在与未来》,邹乐山译,改革宗出版社,2014年,第26页
[51] 邓瑞强、赵崇明编《当传统遇上更新:当代基督徒的更新之旅》,香港神学院、基道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vi页。
[52] 邓瑞强、赵崇明编《当传统遇上更新:当代基督徒的更新之旅》,香港神学院、基道出版社,2013年,“序言”第i页。
[53] 米拉德·艾利克森著,阿诺德·休斯塔德编:《基督教神学导论》,陈知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05页。
[54] 《圣经·以弗所书》4:2-6。
[55] 《圣经·以弗所书》4:13。
(本文作者系江苏神学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