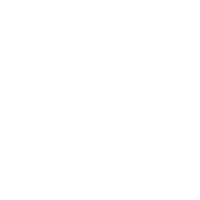编者按:《牧师传奇》是广东教会一位牧者所写的人物传记,传记采用第一人称,以回忆录的方式,讲述了作者的外公孙溥俊老牧师一生中发生在战争年代、建国初期、文革时期、落实宗教政策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等等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感人故事,再现了老一辈牧者忠于上主、忠于信仰、甘心舍己、乐于奉献的精神。愿上帝藉着前辈牧者的见证,激励更多的年轻同工追随主耶稣的脚踪,勤做主工,忠勇向前……
“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 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路加福音18:16
最慈祥——王神荫主教
前两章讲的都是主教给姥爷留下的印象,这一章要讲的却是主教给我留下的印象。
我刚出生三天,姥爷就按照圣公会传统,给我施行了洗礼。满族人家有这样一个习俗:孩子出生三天,要举行“洗三”的仪式 。把父母长辈的金银首饰放入水中,用一根葱搅动,再用葱须蘸水,散在婴儿的额头上、身上,同时念叨:“一洒头,辈辈做王侯……”我想:这并不是迷信,而是一项饱含着祝福的习俗。不过,虽然不是迷信,但姥爷还是没有为我举行洗三,而是选择在这一天为我洗礼(教会传统,婴儿出生第八天受洗,以应主耶稣出生第八天受割礼)。凡受婴儿洗礼或孩童洗礼的人,受洗后,由于年纪还小,不能分辨主的身体,所以不领圣体。一般要等到合适的年龄,领受坚振后,才能领受圣体圣血。
我14岁时,在姥爷的“栽培”下,也背会了许多经文,明白了许多“道理”。于是,姥爷带我远赴山东,领受坚振。而为我坚振的就是当时的山东教区主教,山东省基督教两会主席会长——王神荫主教。
王主教,福建人,曾在国外留学多年,取得了文学硕士、神学博士学位,著作等身,译作颇丰,不仅如此,王主教在圣乐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著有《圣诗考典》一书,文革结束后,主教又用三年时间,写了《新编赞美诗史话》一书。介绍赞美诗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灵性历程,几十年来,这本书多次再版,一直深受信众喜爱。
关于王主教的这一切,都是我上了大学后通过网络才知道的。当年那个懵懂少年的心中,对这次的山东之行充满了好奇:主教是什么样子?他是使徒的继承人,那一定身材高大、满脸虬须,就像圣画中的老约翰一样。他会不会也像使徒那样,可以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姥爷说,坚振就是藉主教的按手领受圣灵,圣经中,主受洗时,圣灵犹如鸽子一般降下,那我坚振时,圣灵会不会也像鸽子一样降下呢?在火车轮子和铁轨“轰隆隆”的摩擦声中,我的思绪信马由缰地驰骋着,虽然不着边际,却也使我的旅途不寂寞,三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和姥爷平安到达山东。
王主教年事已高,近年来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所以就在家休养,老人在他的卧室兼书房接待了我和姥爷。主教安排我坐在长沙发上,让我像本地教会的孩子一样叫他主教爷爷,还拿糖果给我吃,他自己则和姥爷分别坐在两张单人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原来主教和我想象中的一点也不一样 ,他虽然身材高大,但却不是满脸虬须,相反,主教把下巴和脸颊刮得很干净,呵呵,就像他光光的头顶一样。山东人说话的口音很“硬”,所以东北人管山东人叫“山东棒子”,而王主教是福建人,闽南语“质地柔软”,王主教在山东生活多年,将两种语言“有机结合”,他的语调听起来使人倍感舒服,旅途困倦的我坐在沙发上,闭着眼睛听着两位老人的对话,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主日,主教在堂里为包括我在内的十几位年龄相仿的少年实行坚振。由于联合礼拜多年,主教也不便再穿着主教袍服和嘎巴了,他只是穿了一件扎花袖口的白色圣袍,佩着一条鲜红的、绣有十字架图案的圣带,端坐在太师椅上。我们依次跪倒在主教膝前,主教用拇指在一个精致的小盒子里,蘸一点芳香扑鼻的膏油在我们的额头上画个十字,并为我们按手祷告,最后,把一块纪念圣牌挂在我们的脖子上。 坚振礼后,举行了圣餐仪式。我是第一次领圣餐,老实说,心里还有点紧张。分发圣餐的同工告诉我们:“可别用牙齿咬啊。”我领到圣体后,捧在手里,捅了捅旁边一位眉清目秀的白衣少年,问到:“为什么不能用牙齿咬呢?”他一脸严肃地说:“这圣饼是主的身体,主在十字架上都够痛苦的了,你还用牙咬他啊?”听了他的话,我差点笑出声来,结果马上被后排的大妈呵斥:“不许说话,严肃点”……
第三天早上,姥爷带我去向主教辞行,我们要回去了。主教笑眯眯地看着我,宽厚的大手抚摸着我的头,说了许多诸如“要依靠主,勇敢地为主作见证”,“分别为圣,不能羞辱主名”之类的话,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最后,主教送我一枚刻有十字架图案的银戒指,并亲自把我们送上公交车。车开出老远了,我还看见主教站在那向我们挥手。不知为什么,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出来,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不舍。回头看看姥爷,他的表情严肃极了,但我分明看见,老人的眼中也满含泪水……
1997年12月26日的下午,我正和一帮与我一样在教会院里长大的小伙伴疯抢圣诞树上的小公仔、小礼物时,姥爷突然急匆匆走来,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刚接到电话,山东的主教爷爷过世了。”我大吃一惊,眼里的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滴在我的手上,滴在那枚主教爷爷送我的戒指上……姥爷嘱咐了我两句,就急匆匆地赶当晚的火车去山东参加主教的追思礼拜了。
将近二十年过去了,当年的一幕还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那样清晰,仿佛就在昨天,可是猛醒之间才发现,姥爷离开我也已经整整五年了。还记得姥爷病重时,我回老家看望他,望着老人日渐消瘦的脸庞,我泪流满面。姥爷拉着我的手,说:“好孩子,别难过,姥爷侍奉上帝60年,就算上帝真的要召我回去了,那也是好事,姥爷不会寂寞的,还记得山东的主教爷爷吗?还有我的大师兄,和当年一起来东北传教的师兄弟们,他们都会陪着我,一起侍立主前,每日赞美不息……”
对于基督徒来说,离世是一个肉体生命的结束,但同时也是另一崭新生命的开始。我坚信,在一个美好的所在,主教爷爷、姥爷、还有许许多多上帝忠心的仆人正相聚在一起……

(未完待续)
注:本文作者系广东教会一名牧师。